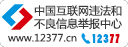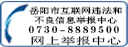有幸生活在香草美人的原乡,身边是一座座自然长成的楚辞植物园,我却识不得几种花和树,更不用说博物和格物了。取兵的新书《洞庭草木深》正好给我补一课,且是必补的家乡风物课和田野调查课。
给我们共同的家园建一座文学化的植物园,厚植土,多栽种,源源输送营养液,于四季轮回中尽情享受乡土之酽、陶潜之乐、舌尖之福、安梦之静、自然之趣,这该是取兵在时光里越法宏盛的愿景。走进这座园子,他当上一个兴奋而尽职的导游,见物说物,引类其事,娓娓道来,博学说开,特别让我这等植物学的门外汉恶补了知识,对平常多见的葛桑麻、桃桂樟们,总算弄清了纲属科目、生长习性、多重价值及附着其上的情趣情怀,它们衍生着道不完的传说故事,守望着土地生长出的无尽秘密。说着说着,那些野生植物都成了他家的乡邻、他家的器具、他家的粮仓、他家的酒藏、他家的茶道、他家的四季菜谱、他家的果盘小吃,物尽其用而不觉用者贪,反而觉得,本该如此,自然而然。为何?作者在每一种植物身上均化进了自己,有他的成长年轮,有他的记忆印渍,有他的隐痛和快意,有他亲人们的烟火日子和命运寓言,说到情深处,“真想把自己活成一朵荷,不为懂的,只为慈悲。”这好像是席慕容的某一句诗的化用。即便是化用,也化得妙,有如化蝶,深情羽化出翅膀,植物充满着灵性,它们循着中国文脉开创的心境物境合而为一的境界飞翔,在那里,无名氏于野外在倾听也在观察:“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屈原在传说中与自己相逢:“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陶渊明在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孟浩然在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苏东坡欣然候着“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在《诗品序》中道出了诗歌咏物抒情所要遵循的要义。这也是取兵所追求的散文之神凝。
唯有诗化的心灵才热衷于移情化物,而个人化的物候书写有了成就审美化人生的可能。在此意义上,我愿把我走进的园子,我打开感官所感知的满园花草树木,当成取兵自家的“大观园”,他的“梅妻鹤子”,他的“诗意栖居”。一个人若果真能安置这样一座园子,他是有福的。说道者爱讲“心外无物”,因我功德不满,我总怀疑那是一种语言般若,说得不客气,就是一种修辞轮空,所指和能指断裂后滑进了玄学的空转。魏晋人士喜玄言,永嘉时代有了玄言诗。钟嵘对玄言诗没好感,认为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陶渊明是从玄言诗的虚化影子里走出来的,他的田园诗布满着日常所见的风物,富有生活气息,既观乎宇宙之所变,又寄身于寻常巷陌,他是物化中的隐者、热爱生命者,他吟颂他万物之中的栖居:“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诗写到这境界,大白话也诗味满满,不止是众鸟欣然,吾辈亦心神向往。正因为陶渊明没把自己放置在玄而又玄的修辞转轮中,他的诗才满是“雅人心中的胜概”。胜概何来?想必要由草木情深所催发,要由家园风物来烘托,那样一座草木扶疏、鸟鸣于巢、阳光南风笼罩着的草庐,便是人间胜境,往高处说,是中国诗化文化的地理标志,是诗化心灵的万流归宗。取兵在他的文集中,忍不住要多次发出“夫复何求”的喟叹,他追求的正是这样的“胜概”。他深恋的家园里,遍布草木,一草一木皆有情有义,形神俱备,妙用多多。他颠覆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的武断,“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花犹如此,何况乎人?取兵汲取了诗人无隔有境的感知书写方式,大书对草木的人性方式、审美范式:“人于草木,焉能无情”。进而,他赋予洞庭草木人格化、活态化、个性化、个人化,打通了人与草木的天然壁垒,畅然行文气,使人与物双向交流互感。这一切,由于是洞庭湖畔、临湘山村的物语人情,又特别具象、亲近、触手可及,让人油然生出一种美妙冲动:明天,该逃离喧闹之城,要么乘舟,深入洞庭腹地去看芦苇水鸟;要么回家乡,像一只欢快、认路的狗,到处嗅嗅,一路撒野……
只有对草木一往情深者,才可能不断将冲动付诸行动。作者正是这样的行动派,他大约是天然的田野侦探,要向大自然探寻并索引它散漫留下的馈赠和密码。这会不会是他一生执着的雅好呢?但愿。明朝遗老张岱总结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张岱自己就是一个十足的痴汉,痴于山水、园林、花鸟、梨园、鼓吹、烟火、骏马、古董、考据、茶道、美食,当然还有写作与做梦;在《陶庵梦忆》中,他写了一个名叫金乳生的园艺师,一生痴爱花草,宅前构花圃,四季轮植数百种奇花异草,烂熳如绣。弱质多病的金乳生每天早起,不盥不栉,匍匐阶下,伺弄花草,细捉虫蚁,“虽千百本,一日必一周之”;“日焦其额,不顾也”。张岱活脱脱写出了金乳生对草花的痴态痴状,激赏之情溢于言表,原来,他们是同道中人。于草木有深情者,古往今来,“德不孤,必有邻”啊!取兵以他深情的文字证明,他也是一个“草木痴”。
寄情山水与草木的散文,张岱写得已近极致,他是小品文的一代宗师。其后,此类散文泛滥开来,特别是现当代更是乱花迷眼,其题材、手法、情愫,无论怎样推陈出新,都难免给人旧瓶装新酒之感。我理解,取兵是情到深处不写不行,痴者自顾,情胜于智,爱好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太讲究章法,何况取兵深知集合大于各部分之和的结构法,他这部新集别出新裁地贴上地域文化的标签,给草木们划了一个同心圆,圆心是洞庭湖,半径是湖湘山水,于是,这些草木就成了我们的乡党,湖湘物候志就有了可触摸体察的温暖感和在场感,读它,犹如倾听乡音在导游,看到熟悉的草木在招手。它们从来平常,却从不吝啬,它们正是东坡先生叹为所止的“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
洞庭草木犹是无边风月,我们该以何种方式欣赏、享受、领悟,也决定着我们的存在质量。
让我没想到的是,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长年居住在南黑森林深处一间滑雪小屋,他深邃的思想受益于大自然的慷慨馈赠:“那种把思想诉诸语言的努力,则像高耸的杉树对抗风暴的场景一样。这种哲学思索可不是隐士对尘世的逃遁,它类似农夫劳作的自然过程。”海氏一改往日的晦涩难懂,明白晓畅地呼吁:“让我们抛开这些屈尊俯就的熟悉和假冒的对‘乡人’的关心,学会严肃地对待那里的原始单纯的生存吧!惟其如此,那种原始单纯的生存才会重新向我们言说它自己”。
从陶渊明到海德格尔,时光流逝了一千五百余年,两者地理距离近万公里。若以另一种计算,从陶渊明的草庐到海德格尔的小屋,本质上是同一个地方:诗意的栖居地;他们也是气质与灵魂上的同类人:诗意的栖居者。他们及其生存方式都令我辈敬仰、神往。作者的《洞庭草木深》也是在体察、践行这种人与自然的共生谐处、交感互动。
我终于明白,一花一草对我如待众生,始终不离不弃,而自己仍是故乡的生客、大自然的看客;我和很多写作者一样,呆在橱窗里看世界,想象世界,思想和生活二者何来亲密无间?往往,我们看不到也听不到——陶渊明在时光的那头遥指那山那水,他的吟哦千年不绝:“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陶渊明思考的问题永远没有过时,我们欲求解的问题可能有千百个,但归结的问题只一个:你是否已抚剑行游,与四季同行,和草木作伴?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岳阳市作协副主席,知名作家、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