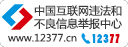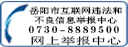在历史理性和情感愿望之间
——评彭东明的长篇小说《坪上村传》

彭东明简介
彭东明,平江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199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共平江县委副书记、《岳阳日报》总编辑、岳阳市文联党组书记,中共岳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岳阳市作协主席。1982年至今共发表短篇小说、散文100余篇、中篇小说38部、长篇小说3部、长篇报告文学6部。
孟繁华简介
孟繁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辽宁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编委。著有《众神狂欢》《1978:激情岁月》《梦幻与宿命》《传媒与文化领导权》《游牧的文学时代》等30余部作品以及《孟繁华文集》十卷。主编文学书籍100余种。2014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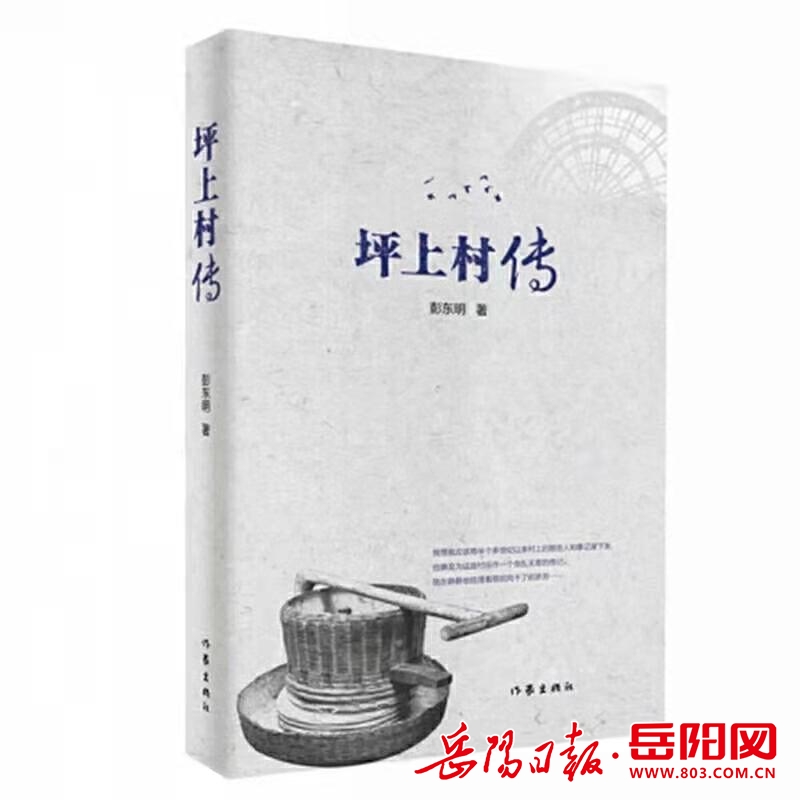
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从题材的角度说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重要变化,但是,乡村题材仍然占有极大的比重。我曾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乡村文明的危机或崩溃,并不意味着乡土文学的终结。对这一危机或崩溃的反映,同样可以成就伟大的作品,就像封建社会大厦将倾却成就了《红楼梦》一样。乡村文明的危机一方面来自新文明的挤压,一方面也为正在构建的都市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和空间。乡村文明讲求秩序、平静和诗意,是中国本土文化构建的文明;都市文化凸显欲望、喧嚣和时尚,是现代多种文明杂交的集散地或大卖场。无论我们对乡村文明怀有怎样复杂的情感,它仍然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脉里。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仍在蓬勃生长的乡村题材小说。
现在我们讨论的《坪上村传》,是作家彭东明新近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传记的方式书写一个村庄的人与事,讲述一个村庄的过去和现在,源于作家挥之难去的一个愿望:在封面题记中彭东明说:“我想我应该将半个多世纪以来村上的那些人和事记录下来,也算是为这座村庄做一个杂乱无章的传记。我在静静地梳理着那些风干了的岁月”。这是彭东明创作《坪上村传》的初衷。这个初衷隐含了彭东明重新发现坪上村秘密的欲望——生活,即便是亲历的,也同样有一个再发现的过程。这也一如沈从文对湘西的书写。如果沈从文没有城市生活经验,那个诗意的湘西是无从发现的。城市给我们以“挫败感”或创伤记忆,这时,曾经的乡村便被滤及为桃花源般的所在,前现代曾经有过的所有的问题被滤及掉了。另一方面,乡村生活中的纯朴关系、真挚情感等,也确有其感人的一面。即便如此,彭东明也无意于对农耕文明的眷恋乃至重塑的立场,以凭吊的情感方式讲述曾经的过去。他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以矛盾或悖论的心情面对正在转型的社会现实,在日常生活和具体的人与事中发现其内在的矛盾和问题——承受这一切的是那些生活在现实中的普通人:村支书老万、村民长贵和他的六个孩子、佬黑、窑匠郑石贵、贺戏子和儿子豆子、陆师傅、彭跋、寡妇水莲、李发、桂花以及彭家的几辈辈老小,他们祖辈生活在坪上村。看到了他们,就看见了坪上村的今天,通过他们,也就与坪上村的历史建立了联系。

作为作家和讲述者,彭东明恰如一个希腊神话的“雅努斯”,一面向着过去,一面向着未来。他要做的,是呈现生活的真实面目而不是解决其中的问题——面对过去,他因文化记忆而“诗话”了乡村,乡村在“再结构”中渐行渐远却诗意盎然,这源于他已经有了“现代”的经验,是“现代”照亮了他的乡村记忆。这一点,他与他的湘籍文学前辈有谱系关系;面对未来,“现代”未必都是好的,但它无可阻挡。“现代”是未竟的方案,它还远远没有完成“试错”过程——那是全新的、有待于证实的未完成性。彭东明的诚恳,就在于他没有回避个人身处其间的真实感受。他是一个来自乡村的知识分子,他走出了乡村,但乡村记忆在“现代”的冲击下反而凸显出来——人们总是倚重已有的经验,已有的经验是可以把握的,一如村民长贵的一生,从生下来便可预知命运的最后;而“现代”是无从把握的,一如小六子,如果没有“现代”的洗礼,那“同性”的取向是无从唤醒的。于是,人们对未知的未来总是怀有先在的畏惧。因此,《坪上村传》无意中实现了两种对话关系,一是同历史的对话,一是同现实以及同类题材的对话。同历史的对话,保有的是作家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情感,曾经拥有的过去并未渐行渐远随风飘散;同现实和同类题材的对话,是彭东明怀有的理性和诚恳的表述。一个十几岁便离开村庄远行的少年,38年的岁月足可以理解“现代”意味着什么。对乡村中国来说,“现代”就是让奶奶和孙子的距离越来越远,就是孙子帮奶奶菜园浇粪的承诺一再落空。
《坪上村传》的形式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作者本人一直在小说之中,他是讲述者,也是当事人。这身置其间的处理方式,强化了小说的“仿真性”,因此也更有真实性的力量。小说没有大开大阖的情节,没有别离的痛苦或归来的欣喜若狂。不经意间,“前现代”逐渐成为历史,“现代”则不期而至——荷香初中毕业辍学到深圳打工,遇到台湾老板,台湾老板为人正派,丧偶,大荷香38岁。向荷香求婚,荷香没有犹豫便答应了。接连给老板生了两个儿子。二妹菜香和名叫胖子的厨子谈恋爱,未婚先孕,孩子生下来后,胖子到坪上村开“情席”餐馆大获成功,迅速开出了连锁店;老三梅香来到深圳,先洗碗后陪酒,然后就睡到税务局长的床上并怀了丁局长的孩子。丁承诺的结婚化为泡影,给梅香一笔钱,梅香将孩子丢给父母自己跑云南去了;老四菊香也来到了深圳,与一个温州小伙子结婚回到了温州,生活平静;老五茶香喜欢读书,父亲长贵阻拦,荷香坚持让茶香读书,一直读到美国留学;老弟老六几次复读没有考上大学,坚决不考了,也随大姐荷香到了深圳。但老六是一个对女孩没兴趣并坚持要求变性的人。固守传统的长贵如五雷轰顶,他根深蒂固的家族“香火”就要断送在老六这一辈。于是,长贵执意要求“我”去做老六的“工作”,希望他幡然悔悟回头是岸,结果是“我”被老六感动,被“工作”了,承认了“同性”的合理性“折羽而归”。在“前现代”和“现代”“遭遇战”中,大概都会莫衷一是进退维谷。通过一件具体的人与事,彭东明真实地表达了处在转型时代的矛盾心态,于是,这个矛盾或悖论就具有了普遍性。
乡村经验或者前现代生活,是自足和封闭的。土地将家族、亲情以及各种利益关系捆绑在一起。家族有几辈人便几辈人生活在一起,其情感关系也因物质和精神的贫困而紧密:“记得,那年我离开村庄时,是一个清冷的有零星雪花飘落的早晨,弯弯曲曲的泥泞的村路上积着残雪,我手里提着一个网袋,袋里装着一身蚂蚁子布做成的衬衣。这种布当时是自家在地里种了棉花,自家纺成纱织成黑白相间的棉布。我不知道为什么村里人要将它叫作蚂蚁子布。提着这一身用蚂蚁布做成的换洗衣衫,我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村庄,后面是我的老祖父、老祖母,祖父、祖母,父亲和母亲,还有我家的那条麻狗在为我送行。我走出去好远,回过头来,发现他们还站在坳口上,且不停地朝前招手,意思是要我莫再回头。”这是前现代家族情感关系最生动的写照。彭东明说:“我在这座小山村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光。这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庄上的人家普遍吃不饱饭,村庄留给我的是一个苦涩的童年,饥饿、寒冷、劳累,充满了我的每一寸记忆。”即便如此,坪上村仍然魂牵梦绕。这就是作家的情感记忆。最后,他还是回到了坪上村的祖屋,当然——那已经是修葺一新、今非昔比的老屋了。
记下那曾经的迷人风情,是彭东明的初衷之一。湖南作家有写风情画的传统,从沈从文到古华、叶蔚林、何立伟等,虽然号称“湘军”,但文字却如沅湘之水,温婉秀丽万种风情。描述这迷人的风情,彭东明是通过源远流长的各种器物、婚丧嫁娶风俗等生活方式实现的。一个香包、一条驮带、一个长命锁、一只瓦桶、几块皮影子、一根短棍、一把油纸伞或一曲童谣,坪上村的风情便迷人了。于是,小说的思乡之愁弥漫四方,或哀婉或凄美或浓或淡,总因其想象的浪漫而充满魅力。但是,这个乡愁之美是只可想象不能经验的。“现代”,并没有证明它有无与伦比的好,但是,现代是历史理性的选择,而乡愁只是个人的情感愿望。在历史理性面前,个人的情感愿望最终将无能为力。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彭东明才“风情万种”地书写了他的“坪上村传”,他“害怕失去”的农耕文明的迷人风情,最终还是要消失在那遥远的地平线上。一如彭东明自述的那样:
村庄四围的矮山依旧,小溪和田野依旧,那飘荡在田野上空的泥土气息和稻子的清香也依然如故……然而,矮山脚下,那一栋栋土坯房却不见了,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栋栋贴着瓷片的楼房。人也陌生了,记忆里的老人,都已经不在了。记忆中的青壮年,现在都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如今的青壮年,我全然不认得了。他们如今的生活,已经不再是原来村庄上那种生活。现在再没人用牛犁田,再无人挑担砍柴,也再无人跋山涉水走长途,再无人纺纱织布。甚至再也看不到屋顶上升起的袅袅炊烟,再也听不到飘荡在田畴上悠悠的山歌……田野上拖拉机、收割机的轰鸣声,代替了往日黄牛和水牛的“哞”叫声,溪边的阡陌早已荒废,水泥公路上“呼”进“呼”出的是汽车和摩托车……水库里的小木船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轰天轰地的机帆船。
彭东明人回到了老屋,但一切物是人非,他还是回不到那个“从前”了——这是“现代”给我们带来的宿命。彭东明的不同,就在于他面对坪上村诚恳地书写了他在历史理性和情感愿望之间的内心矛盾,是这一矛盾结构了这个貌似松散的长篇小说。也恰是这一矛盾,构成了小说的动人力量。现在,彭东明已经记录下了坪上村的人与事,也记下了他记忆和想象中的“从前”,他在实现了自己内心愿望的同时,也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我们面对历史与现实的矛盾处境和心情;他提供了另一种书写乡村中国的文学样式,那散淡如漫水般的文字,也延续了湖湘文学的现代传统。因此,这是一本需要我们重视的长篇小说。
(孟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