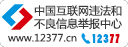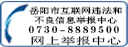青春公田 青涩少年
□一 清
2020年6月5日,我陪央视某摄制组到岳阳踩点,去往铁山水库。在进入公田地界后,车队在我曾用一年多的时间参与修建的公田王家园沙河渡槽前停了下来。当时也不知道因何在这里就停了,总之就是停下了。在渡槽东150米处,一户人家的门口,有位五十多岁的农民在削竹片,他非常友好地与我这个路人打招呼,且邀请进他们家喝口茶。完全是陌生人,能获这样的待遇,内心里有种清凉的暖意。于是,便在他家院前地坪坐了下来,接着便是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约摸三分钟,这家女主人眼直直地望着我,说您是不是长安桥的?我说是啊。她又说,您就是谢万邦老师的儿子吧?您还认得出我么?您是教过我的书的,您是我的老师哩。
我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女主人却继续说,1975年下半年,在公田农中,您教过我们一个学年的书,您还给我们讲《水浒》故事……记起来了么?我叫李金荣。我们班还有李再生、谢大多……
我终于记起来了,但毕竟四十五年前的事了,人的相貌是无法对表的。我所记起的是那一年,我刚从沙河渡槽工地下来,听说大队学校要请个临时老师,替请假了的龚香宇老师代课。当时的校长是谢菊秋,问我干不干。我当然得干,这于我是个极好的机会。于是就替人代课了。这一“代”整两个学期。直到1976年下半年,龚老师休假结束,我才放下“教鞭”,去到另外一个叫苋菜坑的地方喂猪,直到1977年参加中断了十年之久的第一次高考。
都几十年的事了,我竟是以这样一种形式与“公田相遇”。这一天,《岁月留痕——公田传承辑零》编辑组约稿;这一天,正好进入公田踩点;这一天,正好在四十五六年前流汗四百多天修建的沙河渡槽下停车,而停车喝茶的农户竟是我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学生……一切都像是安排好了的。我将这个巧遇发到朋友圈上,微友们都觉得有种不真实的感觉。我也觉得做梦一般。
说起来往事如烟,真就像做梦。这一梦,居然就走过了人生的一多半。
我父亲谢万邦先生是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教师。1961年,国家减少城市人口,我们家除了父亲还保留教职吃公粮外,包括我母亲在内,一家五口一下子就由公户而成农户了。我们从洞庭湖边上的岳阳五中迁回到被城里人称为“三田一洞”的公田区,落户在祖籍铁山公社长安大队。记得那是一个初夏的傍晚,故家的亲戚从公田接我们回大队,在过龙潭沙河时,下堤坡我第一脚踩着的就是一堆牛屎,当时把接我们的人都笑翻了。自此,我就一直生活在长安大队李家生产队。在大队读完了小学,接着在公田中学读初一。不过初一下学期,我就转到甘田公社的“县四中”去了,那是1969年的下半年。有一点要说明,“文革”时的岳阳四中已经改名甘田中学了。之所以转到这儿就读,是因我父亲已从岳阳五中调回了四中。毕竟是原县办中学,包括师资等学习条件,要比公田中学好很多。

(1969年在公田中学读初一)
我读完初中读高中,1972年年底毕业。
说起来,现在很多人都不大相信,我毕业回家的第二天,就在生产队长的吆喝下上了岳阳县小饶港水库工地。我们驻扎在一个叫青隐洞的地方。住所当然是极简陋的,两根树搭成“人”字型,挂上草札,就成了房子。然后在“房子”正中辟一人行道,两边平铺上稻草,两大长溜,就是我们的大通铺。那时候没电,棚内挂一马灯,就是全部的光源。我刚到工地,时年十六,人家看我长得山青水秀的,还很瞧得起我。我刚从学校出来,带了当时很少见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一类的书,很是扎眼。夜间大家也没啥去处,就让我读书给他们听。他们特别喜欢听《阿拉伯民间故事》,这些故事给了他们从未有过的新奇。在那个昏暗的马灯下,我把这本书读了两遍不止,还有人要求再读。我因有晚上读书的付出,白天大家还是很照顾我。当时工地上挑土是记筹的,就是说,你从山坡上挑一担土倒在艰难地“长”高的大坝上,然后从蹲在山坎上的一发筹人手中取回个筹码。这样的筹码一天得完成60个,才算一工作日。我的筹码有时不大够这数,大家也把眼睛半睁半闭的,就算是对我的照顾了。我因之一直很感谢这些爱护着我的同棚工友们。
1972年的冬天可是个大雪冬。那一年的春节,我居然就被留在工地上守铺。与我同留下的都是家庭成份有些问题的,一个叫谢田圭,一个叫谢海江,还有个叫谢亚平。他们三人的家庭成份分别是地主、富农、上中农。而我的家庭成份是小土地出租。那个年段里,这都是不太受待见的身份标识。从民工们回家过年那天起,就一直下着雪。当时工地负责人说,你们就在这守着,明天大队就会派人送来大米的,饿不着你们。但是一直到大年三十夜,也没有送粮来。一则是大雪封路了,且在年关,谁愿意去挣这个工分大老远的送粮?二则可能人家早就忘了青隐洞里还有人等着吃饭。我们当时都十几岁,也没有想得太多,倒是因为不需要出门挑土记筹,很觉轻松,还能赚工分。于是,拆了个被大雪压倒的工棚,抽出里边的木条木柱,在厨房里烧起了大火。我们索性把铺卷挪到厨房里来,那一个温暖热呼啊,就觉得比回家过年更有意思了。于是,我们几人钻入被子瞎聊瞎侃,天南海北的。聊着聊着就饿了,我们就去往青隐洞一些山民的菜地里偷白菜吃。偷的东西煮着吃,那个香味,至今还记得。说实话,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也不埋怨谁,就感到这是一份难得、没有人管的、自由自在的快乐。
在小饶港水库一直干了两年,后来就说水库修好了,还得有渠道、有渡槽,这样才能形成灌溉。于是我们就撤到了大沙河,修筑跨河大渡槽(也就是今天我停车的地方这个渡槽),这一干就是一年多。接下来,我干上了代课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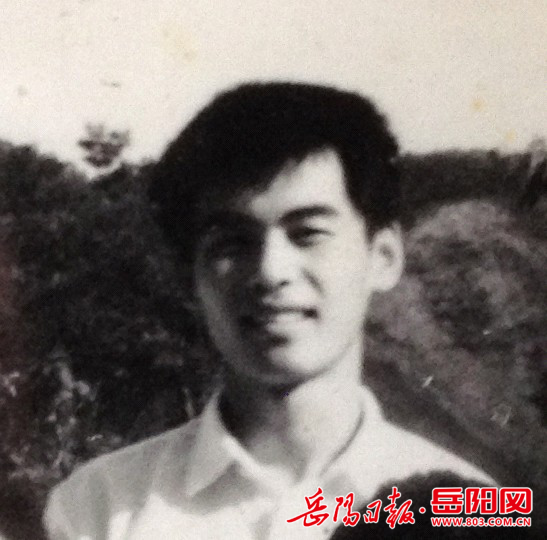
(1976年在公田农业中学当代课老师)
说实话,结束代课老师“生涯”,一时有些茫然,有些留恋。记得那个下学期开学,我也到学校去了,因为我不知道龚香宇老师的假期结束了,也没有人通知我说不用来了。他们都是好意,不想断然地告诉我不能再当老师了。但我不知道啊。还是去了。到学校后,谢小年、谢林庚、谢绪保其实都是看到了我的,但他们都躲着我不与我打招呼,他们都是善良的,怕让我尴尬。特别是林庚老师的一个眼神,让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有些沮丧地离开了学校,按队上的安排去了大河对面的一个叫苋菜坑的大山里喂猪去了。
由代课教师到猪倌身份的变化,我很快就适应了,同时便觉出了那一份的好来。我喂的猪不多,但看的书却是不少。在夜晚的柴油灯下,听着山里的各种虫豸的叫声,很享受。也不知道从哪里弄了套《红楼梦》带上了山,没事就背着玩。先是背里边的判词、诗联,背着背着便“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大段大段地背将起来,竟获整章整章的记忆存储。这实在算是童子功。好像感到自己都成古人了,不知天高地厚地写了篇《苋菜坑赋》,还用毛笔写在猪棚土墙上,起笔是“耸立巴陵之境,起自幕阜之麓”,被当地熊山一位蓄须老者发现,颇有谬赞。
此后不久,传来了粉碎四人帮,又传来了高考恢复。所以,我高考作文写起来还是很轻松的,一韵到底。这得益于我在山上背书的努力。我的高考作文《心中有话向党说》由于当时表达的一些情绪被还在乍暖还寒的政治气氛中的改卷老师判了零分,后来在省、地教育机构的复查下,又给了个满分,且在改卷结束后立即成为手抄本,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并影响到了此后至少连续不少于三届的高考学生,是当时考生必读的范文。该文在我进入湖南师院岳阳分院就读时,正好由《湖南教育》杂志发表。

(1977级新生进校当天《湖南教育》杂志发表高考作文《心中有话向党说》)
自此,我就离开了公田,至少是户口离开了。
有关公田的记忆,都是青涩的,是青春的。这里还有几件相关的事,正与此青涩相关联。一是1968年的公田中学,那时就是在一个山坡上建了两栋房子,每栋好像是三个教室,很简陋。隔着一个土操场,上面还有些旧民居改建的教室。我第一次离开家住外面,应该就是在公田中学。当时学校选我参加了文艺宣传队,晚上要排练《东方红》舞,我得住下来。第一次离开家里亲人,心里很难受。就在落日烧着西边天际晚霞时,我伤心得直落泪,竟自一人在球场边的石条凳上大哭起来。
另一个记忆是,公田中学虽然建起来了,但没有课桌,老师就组织我们到很远的小洞、狮堂里去抬树木回来打课桌;没有柴烧,也是老师组织去老远的东淇洞、仙人石检干柴。因为年龄实在是有些小,挑不了多少。但高年级的同学还是挺努力的,大家比赛似的,尽可能地挑得更多。那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气氛。
从1968到1977,我从公田而甘田,再回到公田的小饶港水库和沙河渡槽,这是十年。1977年底有关公田的故事就是那一年的高考,是在年底进行的。12月17日,我们大队开了一手扶拖拉机,把参考的十多位考生送到了公田中学附近一个叫盐井的生产队,在那里集中由大队做饭招待我们这些考生。那天天很冷,早晨坐在手扶拖拉机上,风刮得脸上生痛。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在公田中学高中部第一栋房子的中间教室,我完成了有纪念意义的这一次高考。
生命中有关公田的所有记忆都是青春的,也是青涩的。公田的一些生活细节常常出现在我此后的梦里,这或者是一种青春的追念吧。
(一清,原名谢柳青,文化学者,中国名博沙龙主席,中国网络电视台公益广告艺委会艺术总监,中宣部“中国梦”公益诗词创作人,《紫光阁》时评专栏作家,《诗画中国梦》作者,《环球财经》杂志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