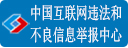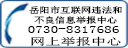威尼斯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依靠海洋贸易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艺术遗存。如今其主岛成为了一座“城市博物馆”——一座漂浮在海上的露天博物馆,每座宫殿、教堂、仓库、会堂、桥梁以及造船厂都是展示于城市空间中的作品。现代的威尼斯人又利用其雄厚的文化资本,建立起强大的博物馆体系和双年展等文化盛会,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和艺术爱好者蜂拥而至的同时,居住在主岛上的本地居民却日益减少。以至于在近期意大利政府反复讨论限制游客人数以及游客进入主岛是否收取门票等事宜。

军械库展览现场
19世纪以来,无论罗斯金还是托马斯·曼笔下的威尼斯,都是一种北方欧洲对于其精神家园的合理想象,威尼斯变成了一种略带东方情调的、精致性感的、颓废的放纵之都。两年一度的威尼斯双年展似乎就是这种放纵的当代表现形式。本届双年展秉承了一贯包罗万象的宏大主题——“艺术万岁”,再次强调了艺术的普世性及其责任。艺术的普世性可能是艺术永恒的主题,在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下,策展人往往难以把握具体作品的展陈以及其在展览中的作用。策展人所构建到的九个“跨展馆”分主题,虽然打破了固有的展览空间,而这些看似毫无关联且轻松随意的分主题,也成了一些媒体诟病的对象。对于艺术的热情和艺术的强大功用,是策展人反复强调主旨,但在这样热烈的主题之下,中国方面的反应似乎并不强烈。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趋冷,各大民营企业对于艺术资助的降温,以及中国艺术界自身的发展,人们对于威尼斯的盲目崇拜已经趋于平静。双年展开幕的人潮过后,展区的人流似乎少了很多,相较前两届双年展,尤其是中国参展与相关工作人员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的2013年双年展:那一年的5、6月份,威尼斯的各大展场和街巷中,挤满了来自中国的艺术从业者,就连远离主岛的梅斯特雷和丽都岛,都住满了来自中国的艺术家。而今年的威尼斯,由于主办方的种种限制,中国成批的艺术家和艺术从业者似乎已经所剩无几。

主题展中阿拉伯艺术家Maha Malluh作品
像威尼斯双年展这样的大型国际性双年展,其宏大主题的构建和作品的选择必须要考虑到所谓“政治正确性”;在略显陈词滥调的“政治正确性”的语境下,展览所关注的话题势必包括移民、难民问题、边缘地区以及少数族裔构成的当今国际政治热点问题。在这种语境下,展览难免会出现些许陈词滥调的说教。如在城堡花园主展区占据主要位置的冰岛艺术家埃利亚松的作品“绿灯”简直就是给移民开设的蓝翔技校,一边通过工作坊教授难民学习制作简单的作品,将作品出售的欧元捐给难民慈善组织,一边鼓励观众参与,倾听难民的心声——而实际上,大多数观众只是尴尬地拍照走开,很少坐下来与难民一起分享“制作艺术”的乐趣……从非洲的织物到亚马逊丛林的帐篷、从哈萨克斯坦艺术家的床到阿拉伯艺术家的磁带,策展人在“艺术万岁”这个主题下,挑选的艺术家普遍倾向非洲、中西亚、中南美等地区,充分体现了其对“欠发达地区”的特别关照。但在普遍的政治话题与普世性话语的双年展中,当代艺术自身的前卫性和实验精神实际上打了折扣。

德国馆安妮·英霍夫“浮士德”
相较两个主题展馆,一些国家馆反而更能体现当代艺术的实验性和问题意识。由于场馆空间相对独立,且主题相对具体,参展人员又相对单一,往往可以发现诸多亮点。如德国馆的群体表演艺术、意大利馆和以色列馆诡异的氛围及气味、法国馆的总体装置+音乐表演,加拿大馆的喷水装置以及丹麦馆的整座森林和暗室,都是将展览空间视为一个整体,作品不单单是来填充空间而是与空间产生对话。

中国馆“不息”展览现场
关于中国馆的表现,早已见诸各大艺术媒体。平心而论,比较起来,这是一届较好的中国馆,但需要反思的地方很多,而且其中反映的很多问题已经超出了艺术的范畴。在大的方面讲,比如一直存在的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价值取向的冲突,以及对外文化政策的行政干预等等。错综复杂、面面俱到是中国馆的总体印象,这与策展人的一贯思路密切相关。而策展人所强调的“非翻译心态”,在主观上是一种强势的姿态,带有一种刻意不迎合西方观众的自信。但实际上,有意无意的“翻译”却处处可见,无论是策展人自己画的极尽机巧并带有详细的术语翻译的“八卦图”,还是在现场很多作品的标签中,都有从西方观众视角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阐释的各种“翻译”手段,带有一种难以避免的“自我他者化”倾向——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和政论家弗朗兹·法农都有过类似的论述,即一种在殖民或后殖民语境下,将自我塑造成边缘的、猎奇的以及未开化的特质,来迎合西方的目光。因为在当今大多数西方观众眼中,中国的艺术和文化依然是带有浓厚异国情调的事物。这种“异国情调”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文化上的,另一种是政治上的。但凡中国艺术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迎合就会出现,也塑造了一批又一批“自我他者化”的作品。在当今举国高喊“文化自信”的政策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策划和创造出有力度的,超越了政治和文化异国情调的,具有普世性语言的鲜活的艺术展览和艺术作品,而不应该将已经被当下生活所遗忘的、濒死的“传统文化遗产”展现在世界当代艺术的舞台;还应该避免以往带有文化杂耍性质的艺术展示以及一种强加的“文化自信”。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文化自信”如何产生和“文化”何以“自信”的问题,以及“自信”的文化如何被展示的问题。真正具有魅力的文化无需强调“自信”,它们在当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自信。

以色列馆
在展陈方式和空间利用上,相比丹麦馆的“开放式”空间和德国馆的“半封闭”式空间,以及以色列馆和法国馆的总体性氛围——这些优秀的国家馆几乎都是只有一位艺术家的“一件”作品,中国馆塞入了太多的内容和作品,以至于无法看到和感受“空间”本身。实际上,在威尼斯展览的空间应该也必须是展览的一部分,空间的形态和规格应该和作品或多或少地保持关联,空间的特性以及作品的特性应该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

军械库展览现场
威尼斯和意大利的很多艺术展示空间及展示方式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特性。在威尼斯这样一座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城市博物馆,对其展览空间的讨论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威尼斯双年展的展览空间,尤其是造船厂(Arsenale,俗称“军械库”),由于其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打造威尼斯地中海海上霸主的古老造船厂,其本身不同于现代主义和当代艺术的白盒子——一种取消自身的意义的“外壳”,威尼斯造船厂本身就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现场,本身就是意义强大的所指;再加上展出于其中的作品,构成了双重的现场,造成了意义的叠加。这类“多重现场”叠加的展览方式在意大利比较多见。比如近期在意大利布雷西亚举办的超前卫艺术家米莫·帕拉迪诺的全城展览,就是典型一例:其作品分别展示于古罗马神殿遗址、古罗马剧院、民宅废墟,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建筑综合体、考古博物馆,以及法西斯统治时期翻修的现代广场。古罗马、中世纪早期伦巴底、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的威尼斯统治、现代的墨索里尼政权,以及当代艺术的诸多现场的叠加首先是基于意大利本土极其丰富的各个时代的历史遗存。在意大利这类“叠层”的历史现场随处可见,而在欧洲其他国家则明显没有这么丰富,所以这种展示方式在意大利具有其独特性。

展示在考古博物馆中的当代影像作品
在威尼斯和整个意大利,这类具有多重现场和多重意义的“叠层展示”不胜枚举,值得一提的还有两年一度的伴随威尼斯双年展的平行展——“未来一代艺术奖”。每逢双年展时,俄罗斯平丘克基金会都会租用威尼斯多尔索杜罗区临近大运河的一座文艺复兴宫殿作为展览场地。这座名为Palazzo Contarini Polignac的宫殿是威尼斯最著名的文艺复兴宫殿之一,内部装饰有油画、壁画以及原有的家具陈设,其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构成了强大的意义所指,而展示于其中的当代艺术作品又常常与宫殿空间和陈设产生互动,叠加了新的意义。而往届双年展(2013年)由杰勒马诺·切兰特(Germano Celant)策划的《丁托列托·维多瓦》,则直接利用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圣洛可会堂作为展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文艺复兴后期大师丁托列托为会堂创作的巨幅天顶画和大量其他装饰绘画。而意大利当代抽象画家埃米利奥·维多瓦标志性的圆形抽象画悬挂于其中,造成了年代相隔近五百年,却气质相通的双重现场。记得在2013年和2014年,意大利小城阿雷佐举办了全城当代艺术展。展示在文艺复兴时期瓦萨里本人画满壁画的故居中阿布拉莫维奇的装置作品,以及绘有文艺复兴早期画家弗朗切斯卡最重要壁画作品的圣方济各教堂中安东尼·格姆雷的作品,还有展示于中世纪广场的大型装置作品,这些叠加了多重意义并相得益彰的现场至今令人难忘。

展示在古罗马神殿遗址中的米莫·帕拉迪诺作品
想要理解这种叠加意义的生成,我们先要了解意大利的大中城市的艺术展示和博物馆机制。意大利的艺术博物馆主要分为几种类型:1、美术馆(Pinacoteca),一般是文艺复兴或者巴洛克时期的私人/宗教/政府要员的宅邸或者宫殿,在私人收藏的基础上加上历代补充的收藏而形成;2、教区博物馆/大教堂作品博物馆/市立博物馆,一般是主教堂或者该区域重要教堂附近或者其附属建筑中,展示该教区的宗教艺术作品,包括建筑残片、建筑上的装饰雕塑以及教堂中搬离特定位置的祭坛画等等,一般地位次于城市的主要美术馆(Pinacoteca);3、考古博物馆,一些拥有古代时期,如古罗马和伊特鲁利亚、古希腊或者史前遗迹的城市往往设有地区考古博物馆,一般占用的是修道院等前宗教空间进行展示;4、教堂/修道院综合体博物馆,一个区域内历代形成的宗教建筑综合体,包括修道院、教堂、修士餐厅、寝房等等建筑综合体,往往包含了上千年的建筑历史断层,而后被改为艺术博物馆的用途。(在有些地方,教区博物馆、考古博物馆和教堂综合体博物馆是一体的,但有明确的功能分区);5、现当代美术馆,在一些较大的城市如罗马、米兰、博洛尼亚等,一般是政府出资邀请当代著名建筑师设计新的艺术博物馆,但在一些中小城镇,其现当代艺术博物馆往往都是中世纪或者文艺复兴时期的宽大宅邸或者宫殿,以其特定位置的艺术作品为基础,如锡耶纳的当代美术馆,实际上就利用了中世纪时的Santa Maria della Scala医院,其内部的著名壁画是艺术史中的经典。

展示在文艺复兴壁画之中的米莫·帕拉迪诺作品
意大利诸多的具有叠层意义的展示空间,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当代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像威尼斯造船厂和很多展示当代艺术的文艺复兴宫殿、教堂,实际上最初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替代性空间”,其作为常规展示现当代艺术的whitecube的对立面,确保了当代艺术的前卫性与实验性。但是,鉴于意大利的特殊文化历史遗存,某些“替代性空间”本身的历史与文化意义实际上超过了于其中展示的当代艺术作品,这就是为什么在意大利当代艺术显得并不十分重要的原因。

展示在中世纪教堂之中的米莫·帕拉迪诺作品
当代艺术承载的东西已经太多,如本届双年展的主题,艺术若要“永生”,就需要做减法,甚至减少到只剩空间本身;我们需要更加单纯而不简单的作品,需要对艺术展示空间的重新关注,需要对艺术持久而执着的热情。正如中世纪教堂中质朴的壁画一样,它们对于空间的经营是如此出神入化,它们传达出的意义和真理亘古未变。我们不能忘记,艺术作品在特定空间中的陈列往往就是作品获得视觉意义和美学价值的关键,那些拐弯抹角和故弄玄虚的观念加工在面对人在文化和政治处境时往往只能是画蛇添足。
意大利馆

意大利馆
将“魔法世界”(“Il Mondo magico”)作为主题的意大利馆展出了三位艺术家的作品。 展览的主题源自那不勒斯学者Ernesto De Martino写于二战时期的同名著述。在当下,传统逻辑已经无法解决国际危机的时候,他们将魔法和想象力作为新的信仰。
艺术家Roberto Cuoghi将军械库的长方形建筑空间转化为了一个制作工厂,在这个工厂里,他将模型制作、材料的转换,以耶稣受难式的过程并以一种当代的方式呈现。艺术家Adelita Husni-Bey用影像与装置相结合的方式呈现了一次工作坊。并将自己发明的塔罗牌运用在工作坊中,通过与参与者的互动来讨论一系列性别、种族等问题。
Giorgio Andreotta Calò以文艺复兴时期造船厂巨大船坞的原始空间作为作品的一部分,在黑暗中用密密麻麻如同森林般的绞手架支撑起一个平台将空间垂直分成两个部分。空间上半部分的平台上注满了水,反射出船坞木质房梁的顶。观众从一层进入空间,穿过脚手架丛林上到二楼可以看到另一半世界。此时观者的嗅觉起到了关键作用——经过水分的蒸发使古老造船厂的上半部分弥漫着历史的气息。作品将水置于人之上空,运用魔术般的手法颠倒了物体的位置,使人们不能忽视展场空间本身的重要历史意义。
意大利馆三位艺术家的“魔法”将文学性、戏剧性融入大型总体性装置,并打破了这三者之前的关系,试图重新诠释现实并将其作为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
法国馆

法国馆
艺术家Xavier Veilhan从空间和作品本身两个方面将法国馆转换成了整体的音乐演出现场。他将白盒子空间打破以德国达达艺术家库尔特·施威特斯(Kurt Schwitters)的《墨茲结构》作为灵感来源,将空间打造成了几何感十足的整体装置。在7个月的展览中,艺术家将召集来自全世界不同背景的音乐制作人入驻馆内的录音棚。通过音乐人的现场编排和即兴演绎,艺术家打破了艺术品的唯一所有权,“团队”成为了这件作品的关键词,观众也不再仅仅作为听众而是见证音乐制作过程的参与者。
以色列馆

以色列馆
以色列馆将生物与艺术跨界,艺术家Gel Weinstein的作品“Sun stand still”(太阳依旧当空)将葡萄酒、咖啡等食品发酵后形成的霉菌斑点散布在一层的地面、墙面,以及二层用棉花制造的大型装置。这些食品材料作为以色列民族的集体记忆以气味与斑驳的视觉形式呈现给观众。霉菌作为不断侵蚀并蔓延的生物暗示了时间的流逝与文明兴衰的更迭。
“Sun stand still”(太阳依旧当空)指代圣经中犹太领袖Bin-Nun试图在黑暗降临前击败迦南国王的故事,暗示了人们对拥有可以使时间停止能力的渴望。




b4981f2b-7973-432a-bc44-f281721b715c.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