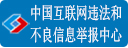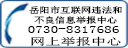现代社会中,要说规矩最多的场所,非寺庙(教堂)、医院和美术馆莫属:
禁止喧哗打闹
禁止穿拖鞋和短裙
禁止携带饮料
关闭铃声和闪光灯……
人们身处其中,毕恭毕敬地面对信仰、生命和艺术。
寺庙与医院的肃穆并不难理解,毕竟神灵就在高处端坐,生命与死亡也时刻都在真实发生。至于美术馆,纵使嘴上不说,人们心中也难免有过腹诽:那些进了美术馆的,一定都是“艺术”吗?
这样的疑窦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尚不存在。十九世纪之前,人们对所谓“艺术”并无太多争议——普桑、伦勃朗等一代代大师们的探索已为艺术建立起了一整套清晰的技术与审美标准。沙龙评审们遵循这套规范,在优秀与拙劣,艺术与非艺术之间,做出斩钉截铁的判断与甄别。获得沙龙首肯的艺术品被请入美术馆、博物馆,接受更多人的朝拜。
是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起疑:
什么是艺术?
以及,艺术可以是什么?
▲《物尽其用》宋东 2005年
2005年,艺术家宋东在北京798艺术区东京艺术工程举办了一场名为《物尽其用》的当代艺术展。现场除了一间旧平房的木质建筑框架外,其余的部分均来自于艺术家的母亲赵湘源女士半个多世纪以来积攒的上万件各类老旧残破的日常生活用品。不计其数的针头线脑、瓶瓶罐罐,在成为“艺术品”之前,曾将宋母在北京的两室一厅住所塞得满满当当。
在这场展览中,大量毫不新奇,多数中国人都在祖辈们的家中见过、又在一次次搬家中遗失的展品,令不少观看者现场垂泪不止。有评论说,展览现场展开了一幅“中国变革时代的历史记忆与肖像图”。北京首展之后,《物尽其用》又在韩国光州双年展、德国柏林世界文化宫、英国沃尔索新美术馆、纽约现代美术馆、温哥华美术馆巡回展出。
但若设想,展览结束之后(或在它们进入美术馆以前),所有展品回到生活里,又有谁会再多看它们一眼呢?所谓“艺术品”的身份与价值岂非不复存在?这一切并无稀奇之处,直到进入美术馆。
换句话说,宋东(以及所有“现成品艺术”的创作者们)的创作机窍之一在于,利用了“美术馆”和“艺术”在现代社会里的崇高地位。——并非贬义,毕竟只有在美术馆里,艺术家被允许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诉说与表达,同时,观众也情不自禁地暂时放下生活里的重重戒备,尝试一种更宽容地理解。那些在其他场合中被淹没、忽视,甚至被消音的声音,都在美术馆里,以“艺术”的名义,获得被倾听的机会……但,凭什么呢?
艺术评论家贡培滋认为:支撑艺术家在美术馆中特权地位的,是人们的信任。这信任可能被滥用,就像生活里的所有信任一样。
1917年的美国独立艺术家展览,便是对“滥用信任”的一次警钟。正是那次展览中的弄潮儿,年仅30岁的杜尚,开启了此后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关于“什么是艺术”的争论。
当时展览规定:任何艺术家只要缴纳六美元费用,就可携最多两件展品参展。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便可以进入美术馆参展——这规则很棒,但组织者仍然高估了自己的气度。
当杜尚在第五大道的商店里买下一个普通的平底白瓷小便器,在器具外沿左侧用黑漆签署“R.Mutt 1917”,命名为《泉》,并决定送展之后,委员会还是将这个不但毫无美感可言,并且充满了性暗示的作品拒之门外。尽管,按照规定,它完全合法,但是遵循既有的审美规则,委员会不认为那是艺术。

30岁的杜尚像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试图在优雅庄严的美术馆里开一个色情的玩笑,用“艺术少年犯”来形容当时的他再贴切不过了。只是,没有一个社会愿意选择信任“少年犯”——除非是在美术馆。
被独立艺术家展览拒绝后,《泉》被送到列克星敦大街中央大宫饭店的展出大厅公开展出。当然,不论虔诚的人们如何仔细观察,看到的也仍然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便池,再无其他。但恰是这种显而易见的荒诞,让人们在最初惊愕与骚动之后,逐渐看清了彼此脸上可笑的“艺术崇拜”,并从一种延续多年的“信任惯性”中猛然惊醒——天啊,这家伙原来是在嘲笑我们!
透过这个普通的小便器,杜尚成功地将矛头指向任何一个人在无意识中接受了的时代价值标准——凭什么这不能是艺术?以及,未经思考的信任——凭什么这可以是艺术?
对于那些将《泉》拒之门外的艺术保守派们,杜尚认为:人人都可以创造艺术,只要艺术家认为那是艺术,并对其背景和含义施加影响,那么它就是一件艺术品。艺术的权利当属于创造者。
对于那些认为艺术崇高的人们,他也同时提出警示:别把艺术家太当回事儿,很难说他们不会当着所有人的面,突然咧开嘴:Bazinga!(逗你玩)
小心,可别再轻信了谁——即便是在美术馆里,或者,尤其是在美术馆里。
观念出色,观念艺术才会出色。
——美国犹太艺术家 索尔 · 勒维特
1917年展览后,有传闻《泉》被一位持保守意见的艺术家协会成员砸碎,之后再未现世。但这一次,与《蒙娜丽莎》的失窃不同,人们并不那么感到心痛惋惜。因为,从《泉》开始,杜尚打开的这一全新领域:观念艺术(现成品艺术),有别于过往所有雕塑、绘画作品,其重点不在于实体媒材——它对取悦人们的眼睛不感兴趣,目标在于影响观看者的思想,而思想一旦产生,便永不消失。
因此,尽管《泉》早已不复存在,但杜尚,这位“艺术少年犯”的决心和勇气,却鼓舞了以“对抗一切现行艺术标准”为己任的达达主义,并席卷全世界——在视觉、文学、音乐任何领域,在巴黎、柏林、中国任何地域……哪里存在压抑,哪里需要批判,哪里需要破除,哪里就有达达。
▲《中国绘画史和西方现代艺术简史在洗衣机洗两分钟》黄永砯 1987
1987年12月1日,中国早期现代艺术团体“厦门达达”的发起人之一黄永砯,把一本中国古代美术史(王伯敏所著《中国绘画史》)和一本西方现代美术史(赫伯特·里德所著的《现代绘画简史》)放进洗衣机洗了两分钟。东西方的传统文化象征烂成一团糊状。然后艺术家将搅碎的纸浆书籍放在一个破损的玻璃上,而玻璃又置于一只包装箱上。作品内容与名称同样简单直白暴力,充满破坏性。
为了与现行艺术标准争锋相对(就像叛逆期的年轻人),达达主义甚至不承认自己是艺术,而称自己为“反艺术”。在达达主义者看来,观念艺术一旦产生,自作品进入美术馆的那一刻起,便已经陈旧,等待被颠覆。因此,“达达”试着比任何艺术流派的更迭都更快速和激进,以此来消灭艺术本身,创造一个永远更前卫的世界。
作为“观念主义之父”,此后一个世纪,杜尚在整个现代艺术史中几乎无所不在,对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通俗艺术和观念艺术均产生过重要影响。即便是今天,在国际上炙手可热的华人艺术家们,从艾未未、蔡国强到徐冰、黄永砯,也都无疑继承了杜尚的衣钵。与此同时,他们又从各自所处的时代环境里重新出发,透过创作新的艺术,补充人类理性思维,探索当下环境中尚未被普遍意识到的东西,以此持续赢得、维系着人们在美术馆中对艺术的耐心与信任。
▲《凤凰》徐冰,2008年
《凤凰》是徐冰归国后的第一个大型作品,最初为地产商所创作,后在各地展出。凤与凰每只长达28米,重六吨,全部由建筑垃圾和废弃的劳动工具制作而成。有评论说,这一作品指向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变迁历程,也是一件赋予废弃物新意义的环保主义作品。但徐冰说:“凤凰放在什么地方就是什么样,有点嫁鸡随鸡的意思。”
今天,正如我们所感受到的那样,“艺术”仍然(始终)是一个能够令人情不自禁地心生敬畏的命题。人们期待并且相信,在艺术家们纷纷以挑战、质疑、冲破规则为荣的环境里,好的艺术将会以其独有的方式给人类社会注入新思维。——除了美术馆,哪儿还能给予如此的宽容呢?
大量当代艺术家们也正是利用这种宽容与信任,强迫观看者跟随自己的思维去理解作品,用另一种眼光观看与思考——即便是提醒人们警惕这种信任的杜尚先生,也同样深谙此道。只是,这就给观众们出了一个难题:在这个无上限、无下限的全新游戏规则中,人们还能分辨出所谓“艺术的价值”吗?
▲《顽皮泼洒》(Misc.Spill)卡迪 · 诺兰 1990
混合媒介,尺寸可变
作品是一件分散的装置,包含铝制框、一个汽车保险杠、一辆购物车和一面星条旗,附近散落着管子、煤块和金属路障。关于这一作品,有评论家予以盛赞:“体现了美国主流文化的暴力与浪费,为杜尚和沃霍尔的手法注入了社会政治的重量”,但也拦不住另一些观看者始终认为这更像一个事故现场,只不过发生在美术馆里。
这便是当代艺术的现状,面对几块砖头、一条腌鲨鱼、一张乱糟糟的床、一屋子陶瓷瓜子……永远有人激赏,也永远存在怀疑。那么,“现代艺术到底是不是一个骗局?”不必羞于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美术馆能赋予艺术家们被倾听的特权,那么观众们保持警惕就是必要的。对此,艺术家不但不生气,还主动移交了权利。
自1994年首次个展之后,卡迪 · 诺兰虽然并未停止创作,却退出了主流商业艺术圈,严格控制展览自己的作品,从未出现在官方回顾展或专论中,刻意地回避着权威艺术机构的盖棺定论,甚至慢慢淡化了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几乎隐居。这意味着,艺术家亲手将评论和判断的权利移交到每一个观看艺术作品的个体手中:排除一切干扰,听别人说没用,反正只要有人说好就一定有人唱反调,关键是你得自己来看。想要继续在当代艺术中获取快乐,成为一件需要每个人亲力亲为的事情。
纽约三糖画廊(现已关闭)曾在2006年举办了名为“近似卡迪 · 诺兰:雕塑和出版物,1984-99 Cady Noland Approximately: Sculptures and Editions, 1984-99” 的展览。展览在未经艺术家许可的情况下进行,展出的作品并非原创,而是由四位艺术家依据卡迪 · 诺兰20世纪80-90年代的作品重制,通过“故意达不到仿制对象的水平,激发公众对体验真实作品的渴望与好奇,而后者却始终是难以触及的。”——尽管仿制作品不太够格,但这一创意精髓倒是与卡迪 · 诺兰的一贯作风不谋而合。
一方面,杜尚之后,艺术摆脱画布、石膏等媒材的限制,当代艺术中出现大量行为、声音、空间作品,不同的材料传递不同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观众在空间与时间中去接触,获取复杂而真实的感官感受——毕竟,眼睛看不到双手的感受,“体验真实作品”因此成为必要。
另一方面,过去面对莫奈的《日出》,人人都可以发表喜不喜欢、好不好看的评价。但在当代艺术中,人们追求、探讨的不再局限于视觉审美,而转变成一场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思维角力。问题不再是好不好看、喜不喜欢,甚至不是懂或不懂,而是向艺术品的价值提问:为什么要进行这一创作?关于这一点,切勿寄望于现成的答案。要知道,上一次人们妄图在“欣赏艺术”上偷懒的时候,就被杜尚狠狠取笑了一把。
再回看那场20世纪最著名的艺术公案:《泉》究竟是一场恶作剧,还是开创性的艺术创造?
杜尚最终还是获胜了,此后翻天覆地的艺术局面,已证明其价值。
至于宋东的作品《物尽其用》,究竟是一场艺术家自我陶醉的瞎忙活,还是具有更多深意的艺术作品?
在目睹那份细心与缠绵,体味那种浩大与琐碎之后,每个人都将拥有属于自己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