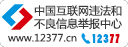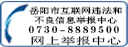山南山北

□江洪渭
一个阳光透射的日子,父亲和我,挑着一床新棉被、一把油亮的算盘和一本皱巴巴的《楚辞》,穿越汨罗江,翻过幕阜山,一脸时间和阳光的风尘,定格在一个破旧的营业所门口。
这是一次比梦还遥远的旅程。这个散发着脱落油漆与腐朽木气息的营业所,接纳了我。一个书生气十足、只会些“六百六”的小职员,因为是农行人,稀里糊涂,当起了信用社辅导员。
那年夏天,县信用联社组织账务规范化验收,每个小组由县联社干部带队,再配一名基层营业所抽来的辅导员。
开“分配会”时,别人乱糟糟选了一番,最后剩下个痴痴的我,和个陌生的南乔。因为还少了名组长,领导就出来发话,说拖一年多了,南乔信用社的防暴设施还未装好,叫县保卫股的一名干部和我去。
于是,一辆破旧的吉普车拖着我和一些笨重的保卫器材,老牛般朝南乔进发了。因不用像别人那样挤公共汽车,一路上,我还有些庆幸。一旁的县干部和司机,却苦瓜张脸。这样盘桓、折腾了四五个钟头,到南乔山脚下时,已下午两点了。
天开始扬起小雨,司机就骂娘:“看那云,再过会,地上只怕可撑船了,就算不下雨,上山也得两三个小时,且难免不出事。”带队的县干部,就面有难色,两人嘀咕了一下,车在山脚下乱吼一通,停下来,县干部说:“唠,马达不行了,这个组长,让给你算了,你上去,只说你是县干部就行。”之后拱拱手,把我卸到山脚下的“慢慢浓”小茶馆,仍拖了保卫器材,和司机一道,骂骂咧咧,打道回府了。
路上半天看不到人,更别说公共汽车了,望着绵绵的雨和黑压压的云,我有些发愁。好在茶店的妇人热心,沏过来杯浓浓的姜盐茶,胸有成竹地叫我等。半晌,果然为我拦了辆拉水的马车。
一路扯谈,赶车老人得知我从县城来,到信用社检查工作,举马鞭的手,就有些激动,指指车上的坛坛罐罐,和一腿野猪肉说,这里也有你的一份咧!
细问,原来老人是信用社的炊事员,在那混了十余年的饭了。快七十的人了,身体出奇的好,老人说,这把“老骨头”,都是水“挑”回的。
原来山上最愁的是水,只要不到镇上买菜,或不来客,一般是不赶马车下山的,嫌慢,且缠脚,常常挑担取水,一条磨得发光的油黑竹扁担,在肩头轻轻地跳跃,即使是摸黑挑水,也不需照明,在这条弯弯的小径上,年复一年爬滚,路上每一块石头,每一处坑洼,路边每一棵杉树,都烙在心头。
言谈中打听到,社里正式职工只有三人:主任姓吴,兼信贷员,因好诗,也有人唤他吴诗人。会计姓林,兼复核员。还有位刚招,叫碧的妹子,出纳兼守库员。
老人话题忽然一转:“县领导,你在上面,管不管分指标?”看到我有些迷惑,他叹了口气:“我是个老临时工咧,吃‘国家粮’怕是难了,好在这把老骨头硬扎,还可以吃几年国家的饭。你是个县干部,给吴主任打个招呼,要他别怕,我还可搞几年饭,不会出事!”
我当时大约被马车颠晕了,有些含糊地点了点头。老人一高兴,便来了精神,马鞭一扬,一串山歌,从九弯十盘的山腰中,抖落出来……
一根嘀格儿的树哎
打一个嘀格儿的床
一个嘀格儿的船船儿哟
配一把嘀格儿的桨
一只嘀格儿的燕哎
绕一柱嘀格儿的梁
一个嘀格儿的姐儿哟
配一个嘀格儿的郎……
缠绵、浪漫的山歌,从一个沧桑的嗓中出来,多了份伤感、忧郁的韵味。一聊,果然。老人年青时,也曾有过喜欢的“嘀格儿的姐”,青春年少时,油菜地里,那谁也给他唱过“慢慢浓”的山歌:
韭菜开花细茸茸
有心恋哥不怕穷
只要我俩情意好哎
冷水泡茶慢慢浓……
上得山,云雾中,错错落落浮出一溜儿灰砖青瓦的矮屋来。还在走廊,就听得算盘噼里啪啦响,轻轻推门进去,两男一女,正在煤油灯下忙碌。听说是来检查的,便放下算盘、账簿争着接袋子、握手,说这么晚了,生怕县干部不来。只有那个长眉白脸的女孩,袖在一堆钞票旁,用扎钞纸,缠绞着修长的手,青涩,一副学生妹子的模样,想必是那位叫碧的小妞了,不免多扫了她两眼。
吴主任忽又记起了什么,问,保卫股的县干部没送防暴设施来?听说车在山脚下抛锚,应是不会来了,就连连叹惜。之后,又忽然高兴起来,搓着手,忙不迭地说,蛮好,蛮好!后来才知,近两年,自吴主任上任以来,我是他们盼来的第一位“县干部”!
山里人好客自然不谈,晚上老吴又带我去拜会了乡党委书记、乡长等,详细不甚记得了。似乎都喝了些酒,似乎这里脸上放着光说,这是我们县农行的领导,那边便说,多来指导工作云云,于是记得,仿佛又举起、又放下……大家就又很高兴。
等拖着碎步,有些朦胧地回到客房,月色稀稀朗朗,从竹枝、树叶、窗户里漏过来,把些鸟瓜模样的图案,淡淡写在弥漫着雪花膏味的床单上。
吴主任兴致却还好,说难得有这个雅兴,又说难得在山里,碰上个读书人。原来他也算是个读书人,参加工作后,又到长沙城里读了几年书,因在职大办过诗刊,一头扎进暴雨,大声朗诵过“天上响雷轰隆隆,坡上石头往下滚”的诗,在学校颇有些名气,本来有机会留校的,但他想到老屋家境不好,下面的三弟四妹又多,挨近些,可以多把只眼睛,照照他们。
谁知回去了,混得并不好,家里也没有谁沾他的光。更令他无言的是,老婆不喜这款酸腐文人,在他读书期间,和位会唱山歌,嘴甜得像蜜的放蜂汉子粘上了,见书呆子在大城市闯荡几年,仍挑了一把算盘、几本破诗回到山中,便又笑他窝囊,终随那汉子,追着一路花香,过着甜蜜的日子去了……
吴诗人还在赊着月色,借着酒兴,神神叨叨,我因为山路颠了一天,有些恍惚,困劲冲上来,也懒得抵挡,斜在床头各自睡去。六月炎炎的夏,半夜竟被冻醒过来,顺手抓过床厚厚的棉絮,拥着,暖暖地睡去……再醒来,天色渐亮,外面一片喧哗,细听,已是鸟声鼎沸了。
轻轻踩着拖鞋,出来看看,才知坠入鸟的海洋了。
多少不知名的鸟,在枝头跳跃,有的拖着长长的尾,在摇曳,有的翘着尖尖的长喙,在轻轻扣打同伴的胸襟,有的是飞起来闪耀一下斑斓的花纹……它们悠闲自在,理直气壮与人分享这一方天地,在街上走走,随意蹲下来,你的四周,会不知不觉落满一圈小鸟,它们看着你,看着初升太阳的羽毛,从小草和你身上缓缓滑过……此刻,如果你拿不出一把细米,或几粒麦子来,你心中会生出一些淡淡的歉意来。
也有我们随处可见的麻雀,那是另一番光景,这里的麻雀,大都乖巧而文静,三五只、六七只,结伴而来,一处换一处散步、觅食,不争不吵、不紧不慢、轻声细语,一副与世无争,清净自如的样子。
漫步南乔的林间、村落,与这些鸟们相处,看它们落落大方在自己的天空、头顶、脚底觅食、追逐、戏闹、歌唱,心里竟生出几分人生的落寞和惆怅。想想山上那个从城市回来的诗人,是一只清瘦、落单、想飞也飞不高的小小鸟吧;而那位孤独一生,煮了十几年饭的临时工古稀人,该是一只又老又丑的鸟了,也许他飞得慢了点,姿势差了点,声音沙哑点,但是无妨,在这片天地之间,在这簇丛林里,他依然在固执地啼唱,寻觅那份属于自己的枝头。
要走的时候,老吴拉着我的手,依依不舍:“感谢县干部放宽政策,还有手续,我们一定会补齐,不会使领导为难的。”我有些不经意地说:“是么,看我怎么查得这么粗心呢。”
老吴便忙叫“老林”“老林”,林会计迅速闪出,把一条相思鸟烟往我的包里塞,我有些发急:“你们说我放宽了政策,又要我收你们的烟,这不是逼我去犯错误?”看到他们尴尬、为难的样子,便接过来,弹出一包,叹一口气:“就一包吧,错误也错不到哪。”他们便有些窘迫地笑了。
转过一个坳,路边一株古老的红杉下,仿佛有甜甜的歌,嫩嫩传出:
高山的流水向东流
我的家呀在桥头
请你请你停个脚呀
把我带回家门口……
原来是碧,递过来一封没贴邮票的信:“这里的邮差,十天半月难上趟山来,我们平常最愁的,就是等信和发信,你在县城工作,寄个信方便。”
我还没来得及说,她就转过脸去:“你帮我发信后,记得写个信告诉我。”也不再回头,像那首还没唱完的歌,悄无声息,湮灭在密密的林海里……
几年后,我调到县农行办公室工作,一次在销毁些旧书报、材料时,无意看到县联社上报来的一份发黄的资料,其中,有关于那次账务规范化验收的。说经最后审定,取消了几个信用社的合格资格,其中南乔信用社验收,因时任组长的县保卫干事缺席,亦属于验收“不规范”,故南乔信用社也未能幸免。
想想那年,我也最终未给她去信。因为那时在山中,我也常为十天半月等不到邮差而发愁,只是那时,我们一个在山南,一个在山北,一个在山顶,一个在山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