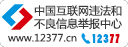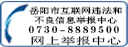□ 杨厚均


一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
刚进五九,汨罗籍作家舒文治给我发来了《百年汨罗小说选》,一路读来,便有一种沿河看柳的感觉。百年文学河流,风景层出不穷。何况这些作品正是出自那条著名的文学之河汨罗江两岸的作家之手。
近年来,汨罗文化兴市的战略已深入人心,汨罗文学活动频繁、佳作迭出、影响日深,已成为一种令人关注的汨罗文学现象。汨罗人做事,有情怀,实在,又大气。这一部由汨罗人编选的由汨罗人创作的《百年汨罗小说选》的出现,是汨罗人典型的文学梦与本土情结的集中展示,是对“蓝墨水上游”的又一次阐释:蓝墨水的上游,不仅指向屈原,也指向屈原开创的文学传统的代代相传。
《百年汨罗小说选》浓缩了百年来汨罗江两岸作家创作的小说代表作,这些作家作品犹如散落在江河两岸的烟柳,预告着一个春天的来临。
二
汨罗江,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
汨罗江流域的文学,同样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因为它体现了它足够的地方性。
并不是熟悉地方,就一定能体现地方性。
地方性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没有面向世界的现代性视野,就没有地方性的自觉。
鲁迅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鲁迅说这话的时候,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正如火如荼。这里的民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地方的。百年来,汨罗江流域文学以其鲜明的地方性汇入现代性的世界文学潮流之中,同时又在中国文学现代性中国经验的形成中彰显出自身独特的存在。
汨罗江在今天的汨罗行政区域版图中不算很长,只有区区60余公里,但就是这区区60余公里流域的范围内,聚集了汨罗江最为厚重与灿烂的历史文化:古罗子国遗址在田畴间隐约可见,屈原投江处日日夜夜涛声依旧,普普通通的山头沟壑,一不小心,依然能翻出国宝级的重要文物,或者依旧寒光闪闪的楚国长剑,在这里,依然活跃着一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十多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似乎在等着百多年前的那一束现代性光芒的烛照,从那一刻起,现代汨罗文学应运而生。拥有汨罗籍贯或者在汨罗生活多年并被汨罗地域文化浸润的作家,创造出了现代汨罗文学。他们一面带着汨罗的DNA融入世界,一面又返回汨罗,重新打量自己,认识自己。
我甚至以为,这一部《百年汨罗小说选》的编选,也是这样的一次出发与返回。
三
彭家煌也许是百年来第一个真正发现汨罗的作家。跟随其舅父杨昌济,从汨罗到长沙、北京,然后落户上海,从乡村到城市,他走了一条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最常见的路,他放眼世界,写下了他对于城市的种种体验,对于新的现代观念的种种理解,《Dismerey 先生》体现了一种世界主义的视野,《皮克的情书》充满了都市爱情的气息,但几乎与此同时,他像鲁迅一样,返身打量他的故乡,以《怂恿》为代表的系列汨罗书写,使他毫无疑义进入那个时代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的行列。《怂恿》因为其“浓厚的地方色彩”被茅盾称为“那时期最好的农民小说之一” 。
并不是每一个走出去的汨罗作家都会回到汨罗书写。康濯、杨沫或出生于汨罗,或祖籍汨罗,他们大路朝天,用新式的现代汉语,书写外面的新世界,解放区、革命、理想、新人的成长,然而,如果你是一个汨罗人,你只要愿意静下心来仔细体会,你依然还是能感觉到那些大故事中的汨罗“土八道”的味道。《我的两家房东》中的那一份认真、那一份善良、那一份平易,《房客》中女主人公的那一份卑微中涌动的倔犟、困顿中等待唤醒的激情与理想,何尝不是汨罗这块厚土中长期积淀而成的隐秘基因?无论他们说的是河北话还是北京话,但都是汨罗河北话或者汨罗北京话。
四
汨罗是个小地方,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如果不是某种机缘巧合,很少会有什么“鳌角色”在汨罗留下来并成就自己。五十多年前的那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为汨罗带来了一个“鳌角色”,那就是韩少功。
“鳌”是汨罗话“厉害”的意思。韩少功是本来就“鳌”,还是来汨罗后才“鳌”起来,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从他各种表述里,可以看出,他反正是喜欢汨罗这个地方的,特别是近几年,他在很多场合干脆就把自己叫做“汨罗人”。他的著名的《文学的“根”》一开始就是从汨罗谈起的,影响了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坛。一个外来人,把汨罗当作了他的根,无论如何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韩少功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外来人书写汨罗的成功范例,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场更为复杂文化景观:赞美与反思,离开与返回,唤醒与沉浸。
《山歌天上来》是韩爹写的?老韩写的?韩老师写的?还是韩主席写的?反正汨罗人会很骄傲地告诉你,那是韩爹写的。
“韩爹”的作品谈论的人太多了,虽然好像似乎都没到点上,但除了和“韩爹”有一种好像似乎与生俱来的“汨罗人”的亲近外,我也没有更好的见解。
还是去看“韩爹”的作品吧。
或者上八景看看“韩爹”种的菜也行。
五
当下的汨罗叙事中,还有一些作家,他们与汨罗的关系颇为特殊,他们自己或者父辈,离开汨罗,又始终保持着某种不舍的联系,他们和汨罗,说近不近,说远不远。既有汨罗的本土认同,更有外来者的观察与审视,他们的写作由此充满了更多的张力。
熊育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考上大学后,大多数时间生活在上海、广州,平时很少回汨罗。开始写诗、写散文,散文获过鲁迅文学奖,后来也写报告文学、写非虚构,近些年来创作了不少大气磅礴的小说。他的创作与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开阔的文学视野很有关联,他追溯历史,叙述历史,寻找自我,他创作的第一个长篇小说《连尔居》,是根据家乡所发生的真实人事生发出来的,这里的故事又和每一个读者关联在一起,逼着你拷问自己。他的第二个长篇《己卯年雨雪》一看日战争期间发生在他家乡的“营田惨案”为背景,将对战争和人性的思考置于宏大的历史叙述之中,显现出作为建筑师的他非常自觉和强烈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据说他正在构想关于故乡的第三部长篇,已构成汨罗叙事的三部曲。
杨本芬老人出生在汨罗江畔,并在此度过美丽又艰难的少女时期,为了生计逃离汨罗,在隔壁的江西成家立业,平时回乡甚少。80岁高龄时出版长篇家庭纪实性小说《秋园》《浮木》《我本芬芳》三部曲,掀起了一股“本芬”热,不事修饰的本色写作和文本深处强烈而深厚的生命意识与乡土意识相得益彰,特别是她汨罗叙事的某些尖锐之处,或许会让本土读者有些不爽,但这一份历经沧桑后的客观冷静,更令人肃然起敬。
还有一个南翔,在南方一所大学任教,做学问,写小说,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他和汨罗的关系纯粹是因为父母,这情形大约和杨沫类似,母亲为了爱情私奔出走,但又无时不牵挂着家乡和亲人,这种复杂的情感神灵一般游弋在她的儿子南翔的生命里,一篇《回乡》交织着两次回汨罗探亲的场景,那份亲情、那份痛楚、那份由家庭而民族的思索,既感性又理性,超越狭隘的地方情感,直击读者的心扉。
六
种过菜的人都知道,经过移栽的菜会长得更壮实,更茂盛。不管是移出去的还是移进来的。
也会有一些例外。菜园里常有一种“欠生”的瓜菜,好像前世欠生一样,土生土长,无人照理,却长得异常茂盛,特别是冬瓜南瓜,又多又结实又好吃。
汨罗文学中有没有这种“欠生”的瓜?除了那些出去的“鳌角色”和外来的“鳌角色”,有没有本地土生土长的未经“移栽”的“鳌角色”?如果有,我要对他们抱以更崇高的敬意,他们靠的可是“硬核”实力。
以我的知识和经验,甘征文就是这样的一位。脚踏坚实的大地,无需更多的参照,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这需要怎样的资质与坚持?甘征文的主要成就是写戏,代表作《八品官》是湖南花鼓戏的经典。他说他写花鼓戏,自己却不看花鼓戏。也是奇事。他也写小说,这里收入的《“老贡献”》,更像是一份特殊年代的小说档案,在这份档案里,我体察出宏大叙事年代一个汨罗人的倔犟,一种无可奈何的同质叙述与痛快淋漓的异质叙述的相生相克。
在我的书柜里,至今还藏着一部八十年代我买过的《畸人传》,这是另外一个土生土长汨罗作家龙楠林的作品,在近六十万字的文字里,我阅读到了同样的一种汨罗人的倔犟:用一种渴望转换又难以转换的笔墨执著而艰难地书写一个酝酿转型又还难以转型的艰难年代的宏大故事。
甘宏大的《过老田的日子》是最近让我大为惊讶的作品。1946年出生的甘老先生离我乡下老家只有一两公里远,之前我从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他几乎没有出过远门,把一双子女拉扯大以后,边带孙子边写作,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作者。和前面提到的两位相比,他的作品少了宏大叙事的负担,地方的真相却更见鲜明、也更具质感,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把一个改嫁女子的心理写得如此细腻,你不得不佩服老人家的与时俱进吧。
在经验、执拗的背后,土生土长的汨罗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执著而浪漫的文学梦,甘征文“甘爹”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表作品,现在八十多岁的“甘爹”还在写,还很享受一帮年轻人喊他“甘哥”,还很活跃。龙楠林写作《畸人传》时已是六十多岁的年纪了。另一位甘宏大“甘爹”在他七十多岁时还一本正经地说:“人的一生应像风一样飞扬。”
这样的浪漫是不是也是汨罗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七
其实我最想说的,还是另外一拨土生土长的更为年轻一代的汨罗作家。
我曾把他们称作新世纪以来汨罗江流域作家群,他们是舒文治、潘绍东、魏建华、蒋人瑞、吴尚平、逆舟、欧阳林,也许还有李卓、南宫浩、一泓、匡瓢,稍早一点有胡厚春、廖宗亮、江异、彭晓立、李丹等,前者常居汨罗,后者时而汨罗,时而长株潭与岳阳,基本上还是没有离开汨罗这块土地。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既面向喧哗的现代世界又不改强烈的汨罗本土情结。
之所以叫做新世纪以来汨罗江流域作家群,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百年现代化走到新世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城市主导的城乡一体化,似乎消解了近百年来的城乡对立,城乡对立视角下的乡村叙事似乎失去了合法性,那么这一时期汨罗人的汨罗叙事还有怎样的意义?二是这一批人的写作与前面提到的一个人有关,那就是韩少功,韩少功2000年移居汨罗八景乡间,对年轻一批的汨罗本土写作者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2021年湖南理工学院韩少功研究所举办了一次学术会议,主题就是“韩少功与新世纪以来的汨罗江流域作家群研究”,汨罗作家向会议提交了一个小册子《到对岸去》,较为详细地讲述了他们与韩少功的关系。
上面所及,第一点关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二点则是一个存在的事实。
关键还是问题。
在一个乡村的意义被城市化所挤兑的年代,韩少功通过他的《马桥词典》、《山南水北》等一系列汨罗叙事再度唤起了汨罗青年作家的地方自觉,不是一种狭隘的地方主义,而是一种胸怀世界面向现代的反思与发现,由此而赋予乡村书写或者地方书写的新的生机。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对于汨罗的近乎矫情的井底之蛙的唱鸣,我们看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看到了热爱以及热爱中的迷惘与无奈,也看到了地方性格的未来品质。在他们这里,乡村与城市,地方与世界,对立又不对立,民情风俗、底层百态、基层世相,总有一些恒定的东西,从历史的深入迤逦而来,千回百转,然后流向远方。
这种恒定的东西,我忍不住要用汨罗话来概括,一是“操空心”,二是“讲鬼话”,三是“蛮绊筋”。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却操尽他人之心,大至远方的世界格局,小至他人的家长里短,评头品足,津津乐道,是谓“操空心”,他们的作品,钟情于这类人物的书写,甚至他们自身就是这样的一类人;“讲鬼话”则表现为对灵异事件和人物书写的巨大兴趣,或者,他们的精神里本身就存在着一个灵异的世界,把它说成是几千年巫楚文化基因的遗传也不为过;“蛮绊筋”更多地指向他们的叙述方式,这是他们和老一辈土生土长汨罗作家最大的区别。他们大都受过西方叙事方法的影响,大都知道有时怎样叙述比叙述什么更重要,因此,也有人把这种叙事称之为“先锋叙事”。但我以为,西方的影响不过是一扇窗口,从这个窗口,他们重新定义了本土“蛮绊筋”的意义,汨罗人的倔犟里,本身就有一种“对着干”的品质:把一个完整的故事打碎,看你能看到什么?
篇幅的关系,这里就不拿他们的作品来一一对号入座了。对号入座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我想说的只是:我对这一拨作家充满了期待。我相信他们还有大动作,还有大作品。
八
总之,这一部《百年汨罗小说选》为我们提出了一个现代汨罗文学的命题。
屈原以来,围绕汨罗和屈原,我们的古人留下了无数经典的诗词文赋,形成了一个丰富而复杂的基因库。
那么,现代呢?这些基因如何遗传,如何变异?
现代小说还只是现代汨罗文学的一支,散文,诗歌,戏剧,还有当下流行的非虚构,都需要进一步整理与研究。
比如前面所说甘征文先生领衔的戏剧,比如当下正火的以《大地上的亲人》和《我的二本学生》为代表的黄灯的非虚构,比如诗歌,印象中有一位从白水去台湾的诗人,笔名楚戈,原名袁德星,在台湾很有影响,也写散文,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画家,还是学者,反“台独”,曾任职台湾故宫博物院。还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听说,汨罗还有一群在外诗人,他们正以另一种精神形态活跃着。
还有一个空间问题。我们这里谈的多是汨罗市政区划内的作家作品。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往往超越行政空间,文学与山水形势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人文地理关联更为密切,汨罗本是一条河流,汨罗文学首先应该是一条河流的文学,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百年汨罗小说选》的选文范围还当扩大,应涵盖汨罗江流域所涉及的江西修水县、湖南平江县、汨罗县、湘阴县、屈原行政区甚至岳阳县部分区域的文学,比如修水的樊建军、平江的张步真先生、彭见明彭东明兄弟、湘阴的周瑟瑟等。这其实是一个很大很有意义的话题。
我最后想说,这部由汨罗人编选的《百年汨罗小说选》由一家公益图书馆和本地作协共同策划,本身就是一个好的创意,写与读相得益彰,于现代汨罗文学的自觉和进一步的研究,开了一个好局。“留却一枝河畔柳,明朝犹有远行人”——借唐诗人许浑此句艳诗寄我的期许与别意。 2022年1月28日
作者简介:杨厚均,男,汨罗白水人,1964年4月出生。博士,教授,现任职于湖南理工学院中文学院,研究生导师。汨罗江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韩少功研究所所长。入选湖南省首批新世纪121人才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