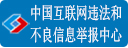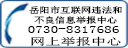《学一学鸽子》
尤金·奥尼尔标志着美国现代悲剧的诞生,同时也开启了美国戏剧欲望书写的阀门。自其之后,阿瑟·米勒、田纳西·威廉斯等美国剧作家,一路将笔触伸向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隐痛,或是美国社会边缘人群的生活状态,书写那些或因无法控制自己情欲而陷入不伦之恋的角色,或是在追求欲望过程中遭遇身心阻碍、被主流社会唾弃的人物。这些作品通过一个个欲望结构出来的寓言呈现在观众面前,在社会对其“无神论”与“性取向”的指责中,塑造出有关美国现代社会的一部部心灵教诲启示录。
这些作品无怪乎为导演提供了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导演蓝本,而对于深受斯坦尼体系影响的中国导演而言,将这些戏剧作为演员体验角色、导演设计调度的练习场,似乎也是顺其自然。然而时至今日,一成不变的排演思路在对观众进行经典教育的同时,是否仍然能够保持这些剧作对观众的吸引力,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越发需要思考的问题。近日,国家大剧院在大、小戏剧场对两部美国二十世纪戏剧作品的同期呈现,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参照。
如果说易卜生曾经为中国戏剧提供了写实主义的摹本,那么尤金·奥尼尔则让中国剧作家看到了如何将写实的笔法幻化为探究人心的万花筒,这也往往让中国剧坛对奥尼尔剧作的排演具有多重致敬的色彩。中国剧坛对《榆树下的欲望》一剧的排演一直秉承忠实原作、严肃认真的态度,相比于对角色动机的挖掘,创作者总是更着力于将剧中的母子不伦之恋呈现得痛彻纠结,从而引发观者同情。但这种欲望一旦沦为演员在台上对角色的自我沉浸与抒情,就极易让观众觉得扭捏作态,从而失去了对剧中角色命运进一步理解的耐心。

《榆树下的欲望》-摄影刘方
此番由青年导演沈亮操刀的“明星”版,再次以尊重经典的态度排演该剧,虽然细节的处理上依然有过度抒情之嫌,但整体上试图达到的“举重若轻”却是值得肯定的。史可饰演的艾碧丰满成熟,而周野芒则赋予了凯勃特这个拥有强烈控制欲的角色以带有个人态度的控制感,在几个瞬间不禁引发观众对这个角色的重新理解,实属难得。就舞台空间而言,在原作中象征生活压抑的榆树与石墙之中,导演选择强化榆树意象,斜躺在舞台上的巨型木板,成为连接两层演出空间(楼上卧室/楼下客厅)的桥梁,同时也为人物行动的心理提供了抒情平台。而第三幕发生在伊本母亲客厅的戏,导演更是让舞台上方悬挂出整整一排倾斜、象征榆树叶子的木片,试图让观众直观感受到榆树般欲望所造就的压抑。
或许是由于导演更熟练于导演歌剧的审美影响,虽然对全剧的掌握已经极力控制,但剧中依旧不免因抒情、咏叹式的处理,遮蔽了对细节二度呈现的更多可能性。比如当伊本在即将与艾碧发生关系的关键时刻,突然将艾碧的脸强行扭转面向观众摆出造型,或是当艾碧杀死婴儿,让白色丝绸沿着木板倾泻而下,观众除了感受到情感的铺陈,通过舞台表演语汇实际并无法感受到导演对角色心理的真正解读。

《榆树下的欲望》-摄影刘方
从国家大剧院戏剧场移动到地下的小剧场,由另一位青年女导演张慧改编、排演的《学一学鸽子》则将我们对美国社会的观察,从十九世纪的新英格兰农舍,转移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纽约下东区的一间阁楼房间。这部由美国剧作家利奥纳德·格许创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百老汇音乐喜剧,原名《蝴蝶是自由的》,后于1972年改编成电影。剧中讲述盲人青年唐尼与邻家女孩吉尔(一个19岁结婚6天后离婚,不相信真爱的女孩),以及唐尼妈妈之间在一天一夜之中发生的冲突。虽然也是讨论普通人对自由/欲望的理解与追求,但该剧并未选择苦情式的结局,而是一边通过盲人的眼睛照见我们心灵的束缚与残疾,一边也以最终团圆的结局赋予观众对自由的希望。

《学一学鸽子》
原作中以蝴蝶象征吉尔性格的奔放与美丽,张慧的改编中则以鸽子替代蝴蝶,以普希金的诗歌“学一学鸽子”置换了原作中的狄更斯的语句,虽然少了几分狂野,但是多了几分贴近中国观众对自由的感知习惯。除了人名、地名上对原作的保留,演员几乎都极力保持一种忠于自我、日常化的表演,这让原作中所有的喜剧元素得以与中国观众的欣赏心理无缝对接,实现了很好的本土化观演效果。然而在失去百老汇歌舞元素或是电影镜头自由调度的帮助后,剧中唐尼母亲与吉尔、与唐尼的大段对话,也为创作者提供了处理的难度。张慧导演对这部剧作的选取,让人联想起她的上部作品《我是月亮》,实际上都是让人在笑中品尝生活的隐痛,而苦涩过后,依然对生活抱有希望的微笑,虽然不是什么大哲学道理,却是每一个生活个体在剧场里所需要的慰藉。
随着近年来国外导演、剧团来华演出的频繁,中国戏剧界在眼花缭乱的导演手法的轰击下,似乎迎来了一种中国戏剧将要拥抱一个崭新开始的假象,但对于这些经典作品的重新排演,却得以让我们不断照见自己真实的创作观念与心态。实际上,当我们注意到那些欧洲当红导演对同为美国经典剧作的排演方式时,就该意识到,我们的戏剧创作本可以更加多元和开放,比如托马斯·奥斯特玛雅导演的《小狐狸》,伊万·范·霍夫对《桥头眺望》的呈现,同样尊重原著,却以演员肢体、舞台空间的运用,赋予原作以重新解读,让观众感受到崭新的视觉冲击。中国导演对经典的排演似乎可以将注意力从如何选取与时代契合的戏剧作品,向如何从原作中挖掘出与社会现实相关的解读方式逐渐调整,从如何让演员实现原作的主题与抒情,向如何通过舞台空间与观演关系的变形赋予原作以新的解读转移,这样中国剧坛对经典剧作的排演或许会拥有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