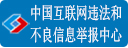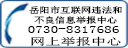为什么那么多艺术家作家赞美计划体制?甚至向往或投靠极权主义?这全都是洗脑或强制的结果吗?难道极权主义的理念和实践,特别是其计划体制模式本身——包括计划经济和计划艺术、计划文化——对艺术家就没有一点影响力、感召力和迷惑性么?《天鹅绒的监狱》一书告诉我们:完全不见得。
对艺术家而言,文化艺术的国家化、计划化至少在三个方面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甚至是难以抗拒的。首先,在物质生活上,计划化和国家化体制解决了市场竞争带来的作家经济收入和物质生活的不稳定,使作家艺术家有了稳定的、甚至是非常体面的生活,因为国家化的作家艺术家是被包养的——当然,前提是交出自由成为御用文人;其次,计划化和国家化成就了作家的“精神导师”“舆论领袖”情结,实现了艺术家“社会园艺师”“灵魂工程师”的梦想,这在市场经济国家同样是不可思议的;最后,国家化和计划化让艺术家具有融入到“大我”(一个虚幻却感觉到真实的集体)之中的归宿感,免于自由市场经济社会艺术家的孤独感。正如美国学者塔米尔说的:那种最鼓励多样性的、最自由的文化,不见得一定比别的文化对作家艺术家更有吸引力。“许多个体发现一种由极权主义文化提供的闭关、团结以及安全的感觉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陶东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20页)
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给了艺术家以自由,免于其对宫廷和教会的依附,但同时把艺术家投放到风险巨大的市场,无法保证艺术家生活方面的稳定性和精神领域、舆论领域的影响力。在资本主义时代,“独立艺术家的生活总是危机四伏,优质的文化迈不出贫民窟。”(第33页),而“只要进入国家认可和接受的行列,它们(艺术)就不会因为缺乏市场而惨遭淘汰,国家保障了其受众。管制亦是一种保护。”(第54页)都说艺术家珍爱自由、自主、独立、反权威,热衷于反抗,都说“自由是艺术的必要条件”,“艺术是自由的同盟”,都说“任何背离艺术的反权威本质的努力都会将艺术扼杀;真正的艺术家都是独立的个人”“没有自主性的艺术是伪艺术”(《天鹅绒的监狱》,第21页),如此等等。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艺术家也讨厌竞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包括影响力和声誉的不稳定和物质生活的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性,特别是艺术声誉和社会影响力的不稳定性,恰恰是艺术家深恶痛绝和深为恐惧的——其程度不亚于对压制和不自由的痛恨。国家化的文艺政策正是在这个方面抓住了艺术家的命脉——当然首先是抓住了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生存条件,抓住了他们的胃。没有胃,心何处安家?
在一切计划化的国家,体制实现了对文学艺术的载体(媒体)及艺术家物质条件的全面控制。人民的一切需求,包括文化和艺术需求,都是被国家计划的,是被规划、被控制的“需求”。控制了需求,同时也就控制了艺术家的读者、作品发行量以及声誉和影响力。所以,艺术家和极权主义之间存在根本的利益纠缠。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对艺术进行成功的控制,艺术家的协作和配合“功不可没”(《天鹅绒的监狱》第22页)。哈拉兹蒂写到:“按‘科学’组织起来的工人‘自己的’国家就像一个工厂。经济财务、劳动管理、政治生活和文化活动都被纳入一个分层组织统一管理。作为如今社会总资本的所有者,国家机器同时也成了知识界的代名词——所有的社会、经济、文化知识的监护人”。(同上,第24页)文化艺术也是如此。一切的计划化,就是一切的国家化,包括艺术家及其劳动以及劳动产品(艺术作品)的国家化。“脑力劳动和国家结构就好比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里的肌肉和骨骼。”(同上,第24页)文人成为国家的雇员,文学、艺术、文化领域的机构被称为国家的“宣传部门”。“如今,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培训的人们成为了可靠严密的中产阶级的成员。顶尖专家们则组成了上层阶级,享受无可争辩的特权。所有专家都被赋予了政治责任,因为每个人都是国家雇员。官僚机构管理者物品流通和文化宣传。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知识界没有什么可以失去,除了其独立性,作为回报,它获得了世界的一半,为此它必须提供维护团结和解释权力的服务。”(第25页)这就是艺术家和国家的交易:我养着你,让你出名,让你享受特权,甚至让你进入“权力的心脏”,而作为回报,你必须交出自由、交出独立性和批判性。作者问道:“在这样的革命中,难道艺术还有任何机会保留其反独裁的本质吗?”(第25页)当然不能,恰恰相反,“艺术家,作为情感生活的组织者,在这项转变的实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在革命之前,他们备受无情的市场的折磨,甚至“一无所有”,而如今,“他们却发现自己处于权力的心脏,享受着为人民服务和组织团结的亢奋劲头。”因此,很少有人能顶住“国家艺术家高威望的诱惑”,“艺术家,作为一个群体,已经成为政治精英的一部分,他们都不愿意放弃随之而来的特权”。(第25页)
哈拉兹蒂深刻地道出了知识分子和计划体制合作、迷恋集权主义的秘密:利益的交换,而且艺术家在进行这类交换的时候,大多数好像并不怎么留恋他们的独立性,似乎没有人对之感到“过分沮丧。”(第25页)我们切不可过高地估计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抵抗利益诱惑的能力。作者感叹:“如今只有在蜡像馆博物馆里还能找见独立艺术家的形象,紧挨着有组织的工人的蜡像。独立的艺术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独立的观众。我们生活在一个将反独裁艺术公然谴责为反艺术的社会。”(第25页)独裁艺术成为艺术唯一合法的代表,反独裁艺术就是反艺术。
因此,国家化和计划化,解决了艺术家在资本主义市场中面对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问题。“艺术家怎能反对这样一个未来的国家——这个国家需要艺术家,并且由他们决定社会的品味。他们期望这样的国家不会把他们扔给无情的市场,这预期也的确实现了”(第32-33页)所以,艺术家狂热地加入革命行列、拥抱计划体制并非出于纯粹的利他主义,而是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在内。对市场的恐惧实际上就是对边缘化的恐惧。艺术家热爱自由,但是又惧怕边缘化,而边缘化乃是自由的代价。




b4981f2b-7973-432a-bc44-f281721b715c.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