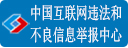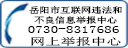薛忆沩出生于1964年4月,他很喜欢自己出生的这个年月,因为正好与莎士比亚出生的日子相隔四百年。
这是一种偶然,或者说是一种宿命,而薛忆沩相信宿命。莎士比亚令他心生敬畏,他曾在十八个月里,几乎每天都拿出一段时间来研读莎士比亚的原著,甚至想过要将莎翁的全部著作译成中文。他经常对人说,“凭着对莎士比亚的敬畏,我就可以放弃自己的写作,他总是给我带来惊奇。”
然而,对文学的激情和对语言的执迷,让他不可能真正放下心中的写作事业。他学理工科出身,学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最前沿的计算机专业;他对数学充满热情,欣赏它可以以极简约的公式解释复杂的世界;他也酷爱哲学的逻辑思辨,他的思维中有极理性而深邃的一面。然而,他又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人,他曾说自己的每篇作品都是这种敏感的见证,他的内心充满了脆弱的感性。
许多媒体将薛忆沩称为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的确,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文学作品,薛忆沩都给人“不入俗流”之感。他主动疏离于文学圈之外,从不参加官方组织的文学活动,也很少与文坛人物往来。因为他相信文学是个人的事业,是孤独的事业,而“孤独是艺术家保护精神世界的‘铜墙铁壁’”。
他的生活方式也“落伍”于时代,比如,他至今不使用手机,不太关心新闻,他对外联络主要靠座机和邮箱。通常五公里以内的路程,他都会选择步行,而非搭乘交通工具。他喜欢跑步和游泳,将其视为对意志和体能的训练。他总是在寻找将生活简化的可能,对外在物质生活的要求极低,而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极高。他曾说,“做时代的落伍者有许多的快感,落伍者可能会保存下一些最精致的趣味。”
1988年8月,《作家》杂志用头条刊发了他的中篇处女作《睡星》,开启了他的作家生涯。随后,他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遗弃》,那年他24岁。这部原名为“业余哲学家”的作品,受到刘再复、何怀宏、周国平等人的高度赞赏,却在长时间内被市场冷落,直到多年后他“重写”此书。1991年,他的微型小说《生活中的细节》与王小波的中篇小说《黄金时代》,一同摘得台湾《联合报》小说奖。然而,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很快就消失在文学的视野里。
此后多年,薛忆沩的文学出版一直不太顺遂,他自嘲为“好文学的坏运气”。2002年,他移居蒙特利尔,在这座主要使用英法两种语言的城市,他仍然坚持用母语写作。他用不懈的坚持为自己“转运”,迎来了此后的“文学爆发”,他的《遗弃》《空巢》《深圳人》《首战告捷》等作品,接连获得媒体颁发的“年度好书”、“中国影响力图书”、“年度小说家”等奖项。一些作品被陆续翻译成英文、法文、瑞典文,并在国外收获奖项和口碑。
他很欣赏苏珊·桑塔格的一句话,“拥有一种语言,就是拥有一块疆域。”他认为,一个对语言有感情的人,不应该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因为拥有广阔的疆域会使人博爱。薛忆沩是语言学博士,他对语言的痴迷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读懂这门语言最好的文学作品,这位生活的极简主义者,在语言中寻找自己的天堂。
2018年7月,他出版了随笔集《异域的迷宫》和访谈集《以文学的名义》,首次讲述他在异域十六年的求学和生活经历。这位总是在小说中“表现历史的荒谬和生命的复杂”的作家,将笔触对准了自己。他将异域比作迷宫,而“抵达”总是一次朝向迷宫的冒险:“因为几乎所有关于目的地的想象都是错误的。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中的‘抵达之谜’。”
谈圈子主动与“文学圈”保持疏远
新京报:从1988年发表中篇处女作《睡星》算起,你进入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已整整三十年。你肯定自己的文学道路是“一条从没有人走过的路”,并且说这“异类”的文学之路并不是自觉的选择,而是不得不服从的宿命。为什么?
薛忆沩:我可以用数学上的“反证法”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是自觉的选择,我不可能坚持到现在,也就是说不可能坚持三十年。回头看去,我个人的“文学三十年”的确充满了戏剧性。我大学毕业于北京航空大学(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但是我没有随波逐流;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到了深圳。那时候,我连发表作品都非常困难,文学梦就像是一场噩梦,而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商海上的“发展平台”对我却不仅是现成的,还好像是定制的,但是我仍然“不识时务”……可以说,经历了诸般曲折,才赢来了后来的“文学爆发”,我不相信自己有如此强悍的“自觉”,我相信这是出于宿命。
新京报:这三十年里,你的作品经常处于文学的中心,而你本人却始终置身于文学界的边缘。你在十年前写过一篇文章,调侃自己“好文学”的“坏运气”。现在回头来看,那“好文学”的“坏运气”是否也和你与文学界的主动疏远有关?你如何看待当前国内文学界的圈子化现象?
薛忆沩:与文学界的主动疏远,也许与我的DNA有关,但是更重要的却是基于我对文学的信念,我觉得文学不应该受组织关系的纠缠和制约。坦率地说,我并不是与官方的文学组织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发表我作品的许多杂志都是属于各级作家协会。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差不多停留在那种“低端”的水平。
我也经常会听到读者、编辑或者作家抱怨文学界圈子化的现象。我印象中那并不是“当前”才有的现象。常识就足以告诉我们,小圈子一定会妨碍文学的大发展,就像保护主义一定会对经济产生制约一样。特别地,我想说,小圈子是最容易让年轻作家中招的陷阱,是年轻作家的灾难。我希望有才华的年轻作家对此高度警惕。年轻作家不妨给自己定一个可能永远也达不到的目标,比如要写出从来没有人写出过的作品,同时永远盯住文学金字塔的尖顶,千万不要落入世俗的圈套。
新京报:刚才正好提到“好文学”,在你看来,“好文学”的标准是什么?
薛忆沩:这是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回答的问题。《罗素自传》的第一句话,将贯穿他一生的三种激情归结为: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难以承受的同情。我想,是否具备这三种激情,就可以是评判“好文学”的标准。也就是说“好文学”应该是真的、善的、美的,“好文学”也应该是自由的和智慧的,“好文学”更应该是悲天悯人的。
谈艺术如何溶解复杂的现实
新京报:你是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物的?你又如何看待文学的艺术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关系?
薛忆沩:我经常说是我的人物选择了我,而不是相反。其实,这也许更是一种双向的选择。不论怎样,我与人物的关系同样具有浓烈的宿命色彩。这样的例子很多。
比如,《深圳人》第一篇作品里的那位“母亲”。她可以说只是在我眼前一晃而过的一个陌生的身影。那天晚上,我在深南大道东侧海富花园前的草坪上散步。前方一位好像也是在散步的女士的背影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走得很慢,慢得让我感觉她好像有点伤感。我以自己的节奏继续前行。没有想到,刚从她身边走过去的时候,果然听到了她发出的一声长叹。我没有减速,也没有回头。但是,整个故事的轮廓刹那之间就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了。
我一直相信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是第一位的。高超的艺术性能够溶解复杂的现实性。我们读文学作品,不是去欣赏它的现实性,而是去欣赏它的艺术性。毫无疑问,现实一定是浑浊的,但是因为艺术的加工,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显得清澈透明。
新京报:你的许多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没有名字,只有职业或者身份。《深圳人》就是一个典型,出没于其中的是母亲、神童、出租车司机、小贩、剧作家、女秘书、物理老师、文盲、父亲这样一些没有姓名的人物。不给主人公命名的好处是可以建立一种间离感,同时也可以让个体的故事具备象征意义,甚至变成对群体的写照,这是你想取得的效果吗?
薛忆沩:不给主人公命名,其实最开始主要是我克服创作心理障碍的一种手段。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刚尝试小说创作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有名字的人物无法让我写下去,不管这人物叫张三、李四还是王五。一个权宜之计是使用绰号,《睡星》是最早的例子。另一个权宜之计是使用字母,后来收藏在《遗弃》里的那些短篇小说就是这样做的。
到写作《深圳人》的时候,这种技术手段的确变得更有哲学的意味,比如我觉得深圳人的生存状态有点像“出租车司机”,或者一座突然繁荣起来的城市正好可以与“神童”类比。《深圳人》始于“母亲”,终于“父亲”,这也是我的一种故意的安排。而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系列中,我将三篇作品的主人公都统一为X,尽管他们的生活细节并不完全一致。
新京报:你曾说小说的重要使命是表现历史的荒谬,即便是处理当下题材,你的作品也往往表现出冷峻的历史感。为什么会对历史有这样的偏好?而表现生命的复杂也被你视为是小说的重要使命,因此你的作品重对内心活动的捕捉,轻对外部世界的描绘。历史和生命是通过什么力量结合在你的作品里的?
薛忆沩:我经常说我的主题是个体生命与客观历史的冲突。这也许是受了莎士比亚悲剧作品的影响吧。莎士比亚的悲剧总是将个人“生存还是毁灭”的筹码压在历史的天平之上。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的启蒙教育,也特别强调历史对个人的决定作用。
我从《遗弃》(也就是从我创作的源头)开始,就在认真探索客观历史与个体生命的纠缠。年轻的“业余哲学家”通过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生活细节,意识到历史正在走向“混乱”的未来,他选择了“遗弃”。
而在我的战争系列小说中,被卷进历史潮流的个体生命,都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就像《首战告捷》里的那位将军一样。“回哪里去?”是他在小说里说的最后一句话。在所有这些作品里,无法理喻的“偶然性”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我想,将客观历史与个人命运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就是这种无法理喻的“偶然性”。
谈移民 在异域中扩展文学疆域
新京报:三十年来,你的长篇小说只有五部,而且篇幅都不大。你写得更多的是短篇小说。这大概与你奉行的古典主义原则有关,因为短篇小说似乎对叙述的节制和精准有更高的要求。你将来会写“大部头”的作品吗?或者说你有写“史诗”般的作品的野心吗?
薛忆沩:长篇小说论“部”,短篇小说论“篇”,不能进行数量上的比较。从字数上说,我五部长篇小说总的字数,远远超过我全部短篇小说的总字数,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另外是一个主观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我的短篇小说写得比长篇小说好。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总是试图用不同的方式写长篇小说。长篇小说更能满足我对文体的探索欲。
是的,除了《遗弃》之外,我的长篇小说的体量都“偏瘦”。这是我刻意的追求。这当然也与我信奉的节制和精准原则有很大的关系。我将来也不大可能写“大部头”的作品。我不觉得“史诗”般的作品就一定要是“大部头”。《一九八四》可以算是“史诗”般的作品吧,它的篇幅就不大。还有《动物农庄》,它的篇幅就更小了。
有时候,一行诗就足以具备“史诗”的分量,比如波德莱尔的“革命就是用牺牲换取迷信”,比如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我的《上帝选中的摄影师》写了一个人的一生,却只是一篇短篇小说。首先出现在《遗弃》里的《老兵》写的也是一个人的一生,篇幅却只有《上帝选中的摄影师》的三分之一。这两篇小说也许暴露了我有写“史诗”般作品的野心。
新京报:你旅居加拿大已经十六年了,异域生活经验对你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你仍然用母语写作,题材大部分也仍然与中国人的生活相关,时空的转换会让你有隔膜感吗?你如何确保自己对当下中国人生活和精神状态把握的精准性?
薛忆沩:移民生活对作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很多影响是难以解释的。对我来说,移民生活的影响几乎全部是积极正面的。这是我的幸运。
我的创作并不局限于中国人的生活,比如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里就用到了不少蒙特利尔的素材,还有长篇《希拉里、密和、我》里的一个女性主要人物完全不是中国人,另一个女性主要人物是中日的混血儿。又比如,在“战争”系列小说里有形形色色的传教士,在《深圳人》里有来自加拿大的“村姑”等。
尽管如此,时空的转换在特定的时候也还是会让我产生隔膜感,不仅对远方的故乡,也对眼前的异域。这特定的时候就是集体无意识甚嚣尘上的时候。比如,异域的邻居都在为同一桩丑闻义愤填膺的时候,或者故乡的朋友都在为同一段赛事欣喜若狂的时候。集体无意识总是带给我流离失所的感觉。我确保精准性的方法就是盯住个体生活的细节,或者说得更形象一点,就是在集体无意识的大海上,去打捞个体生活的残骸。
新京报:移民作家的文学疆域会因远离故土而缩小,还是会因为获得异域经验而扩大?你如何战胜异域生活中的寂寞?
薛忆沩:我想两种结果都有可能出现。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话题。2005年第一次回国的时候,我去拜会出版界的一位老前辈,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魁北克的独立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深有感叹,对同行的朋友说:“你看,好奇心就是生命力。”我知道,中国绝大多数的移民作家是不具备这种好奇心的。他们不读当地的作品,不逛当地的书店,也自然不懂当地的文学。
最近两年因为翻译作品受到关注,我在英语世界的一些城市有较多的文学活动。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来参加我活动的除了本土作家之外,还有居住在当地的瑞典作家、印度作家、阿富汗作家……但是,我却从来没有遇见过中国作家。如果没有好奇心,移民作家的文学疆域就会因为远离故土而萎缩。毫无疑问,好奇心也是我个人在异域生活中战胜孤独和寂寞的利器。
谈意义 写作是利他的
新京报:布罗茨基曾在一篇关于流亡的随笔中说,异域的生活教给流亡作家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生命的“无意义”。而你在一次访谈里说,从小就对生命的卑微也就是生命的无意义有深切感悟,这种无意义感是否会滑向虚无主义?无意义感与成就感或者价值感是否能和平共处?
薛忆沩:的确,对大多数作家来说,走进另一种语境,走进另一个参考系,虚荣就荡然无存了。我并不觉得这是坏事,因为写作本身是需要距离,需要孤独,需要对“无意义”的体会和感悟。对生命本质的正见会帮助人看到生活的“大图像”,会让人自省,也会让人自由。“无意义”针对的是“我”。认清了这一点,我们会知道生命的意义不在“我”,而在“他”。也就是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利他。牢固的成就感或者价值感,只可能建立在利他主义的基础之上。艺术是利他的。写作是利他的。借用鲁迅的说法,作家是吃草挤奶的“孺子牛”。事实上,文学本身就是无意义感可以与价值感和平共处的见证。
新京报:你现在主要用汉语写作,用英语和法语阅读,你还学习过其他多种西方语言。这种对语言的热爱从何而来?你如何看待语言与文学的关系?
薛忆沩:我对语言的热爱有两大来源:首先,新文化运动最初三十年里的中国作家,大多受过多种语言的熏陶,对他们的敬意自然会滋养对语言的热爱。其次,改革开放为我们这一代在十年浩劫里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送来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现代派文学是在整个西方文化朝着“语言转向”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其中的许多重要作家都是语言的天才,对他们的景仰,也自然会强化对语言的热爱。在我看来,语言不仅是文本的外表,还是文本的血脉。它是真、善、美的有机结合,是文学的第一要素。
新京报:你的《深圳人》受到了乔伊斯《都柏林人》的启发,你又为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写过一部比原作篇幅还长的解读(《与马可·波罗同行》),你还写过《文学的祖国》,一部充满个性的文学评论集……你如何看待文学的传承性问题?你会在意自己的文学地位吗?
薛忆沩:好的写作者首先一定是好的阅读者。这铁定的逻辑就是文学具有传承性的理据。不久前,一位加州大学的教授传来三篇学生作业,是他们读我的作品之后的心得。我没有想到,我那些老派的作品会引起95后的学生那么深的感触。在给那位教授的回复里,我就谈及教育在文学传承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学是一场与时间的搏斗。“好文学”一定是最后能征服时间的作品。从这个角度看,传承对文学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关于传承,一个有趣的现象总是引起我的好奇:文学传承经常是跨文化和无国界的。比如,马尔克斯强调是福克纳将他领进了马孔多,而赛珍珠承认将她推上诺贝尔领奖台的是《水浒传》等中国的古典小说。我非常清楚自己作为写作者的责任,但是我从来都不在意自己的文学地位。这也许是不够成熟的表现吧。如果我还有另一个“文学三十年”,到那时候(也就是到2048年),我也许会变得有点在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