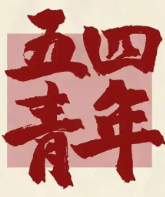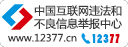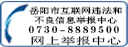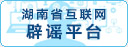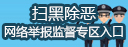◎苏 敢
◎苏 敢
虽然“庸常”一词早已经是我现在生活的入骨描画,但有时候,也还是会有冰火淬心的悲欣跌宕。
大前天,我巧遇一个“失散”多年的同学,一起乘高铁从深圳回湘,一路欢聊,感觉自己又回到了懵懂少年时代;前天,在我曾虚度华年的岳阳城里,与几个老兄弟把酒“日白”,欢乐得忘了自己的年纪;昨天,我家四个兄弟姊妹们一起,给大姐通宵守灵,最后一次陪伴在她身边;今天,我们在雨后泥泞的山路上,送大姐到了她的长眠之穴,完成了和她今生的告别。
我家兄弟姐妹五个,姐姐是老大。我开始记事时,大姐好像就是高中生了。那是上世纪70年代,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山村里,女孩子读书的少,能读到高中毕业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大姐除了带着我们三个兄弟做农活(没有什么妹妹干农活的印象,可能当时她太小),其余时间总是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我上小学时,姐姐高中毕业了。那时候我们农村孩子是没什么机会上大学的——不是考不上,而是根本就没机会去考。人民公社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当然基本上也不会推荐真正的农民子弟。
我对大姐高中毕业后一段时间里的唯一一个记忆,就是当时有人介绍一个“大学生”来相亲,那人瘦瘦的,但很神气的样子。
虽然这事不了了之,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相亲”,所以印象深刻。
但这之后,姐姐带我经历了很多的人生第一次。
大姐高中毕业前后,正是上世纪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尾声,高中毕业后,大姐也就顺利地去了我们公社所在地的“乡镇企业”工作。我也得以跟着姐姐第一次离开我们“大队”(生产大队,与如今的“村”类似),看见了街道和许多卖东西的“铺子”;第一次在镇上的馆子里吃上了“光头面”——没有“码子”的清水面;第一次见到可以把芦苇和稻草变成草纸和瓦楞纸的“造纸厂”;第一次在造纸厂的废纸堆里找到大量的连环画,和各种各样的厚厚的小说——得益于此,我在初中阶段就把那些文学“世界名著”读了个遍;第一次见到造纸厂利用废弃热水建的大澡堂子……
我是兄弟中的老幺,所以放寒暑假时,姐姐经常带着我去她上班的乡镇企业里去玩,造纸厂、鞋楦厂、农机站,包括那里那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我至今都还有印象。
等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已经是1983年了。当时大哥去了曾经的先祖流放之地当兵,来信里面常夹着他穿军装的照片,言语基本上都是指点江山的口气。二哥赶上中国“恢复高考”,凭真本事上了大学。我们的眼中开始有了高山大海、世界潮流,大姐和她朋友们的乡镇企业生活,慢慢满足不了我们蓬勃的好奇心。但在我们兄弟姐妹中,大姐还是很有“范”的。不仅是穿衣,更有口音的改变。
在上个世纪后期,中国的“乡镇上的人”是一个很独特的群体。其语言、形体、行为方式,都有其独特的呈现方式。一方面,他们是乡邻农人眼里的城里人,代表着农人们对城市的想象和认识。另一方面,在县城、地区行署治所、省城的人眼里,他们又成了“农村人”,与他们周围的农民并无二致。所以他们常常被自己到底是凤凰还是家鸡这个命题所折磨。
那时候我们南方山区农村,真的是穷,而且几乎没什么赚钱机会。农民不仅一年到头摸不到钞票,种了粮食,也要先交“公粮”——无偿的,农闲时,则被征调去各种工程上无偿卖苦力。因此,“农民”一词不仅是对一个阶层的职业标注,也是对其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形象描述。
如果有“被人看得起”的身份排行榜,农民二字,铁定倒数第一——更要命的是,这个职业特别容易被终身锁定难以更改。
我们老家把城里人统称为“街上的”,那时农村人白天谈论夜里梦想的群体。他们吃“国家粮”,不至于饿肚子;他们走在干净的石板路上,衣服鞋子四季不沾泥巴;他们抬眼望天,高人一等,说着与几里路外的我们不一样的口音。
为了迅速彰显进了街上人队伍,与昨日之我划清界限,洗脚上岸的“知识青年”们除了努力把握一切机会,拼命“向上钻”,暗地里保持勤奋和听“领导”话的习惯外,他们首先在衣着上迅速与农民亲戚们区分,不仅是有“的确良”等材质,裁剪上也更大胆和新潮。其次是迅速学会了新市古镇人独有的口音,我印象中特别诡异的是他们把“吃”发成“踏”,与四周乡邻迥然不同。
随着“港风内渐”,这个独特的群体在异性交往方面当然也更加大胆。我记得一个似乎是在乡政府工作的女子,大姐的朋友,长得肤白貌美眼波灵动的,有一次向大姐痛诉她被男人始乱终弃,言语中还有那个男人的正牌老婆如何。哭得稀里哗啦的。
可能也受这种氛围的影响,姐姐找的对象也已结过婚。
这件事给我们家沉重一击,一向老实巴交的父亲和睿智大度的母亲为此反应非常激烈,一段时间内家里鸡犬不宁。那年我已经上了大学,暑假返校时,娘送我去搭长途汽车,路上我劝娘对大姐这事别过于计较,娘只是叹息摇头。
在那个没得到祝福的婚礼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大姐很少回家,而即使是我们年节团圆,父母也基本上不提他们能干自立“不听话”的长女了。
参加工作后我很少回家,与大姐也几乎没有联系。偶尔在过年时见到她,发现她精神还挺好,年轻时那种精明和自信也愈发鲜明了。
通过其他亲戚也听说大姐生活得风生水起,在镇上买了一片位置很好的地,也盖起了几层小楼,还做起了自己的买卖,而且在当地圈子里算是混得比较开的。
新世纪后我因为回乡办实体,与姐姐又开始有了联系。中间因为有困难也找过大姐帮忙 ,她很悭吝,我也理解她的来之不易。说实话,毕竟经过生活三十多年的淘洗,我们早已不是同一level的人了。
大姐一生中似乎对“规则”没什么敬畏——包括骑坐摩托车要戴头盔,这一点绝大部分农村人都是如此。而这也最终要了她的命。
那时候我娘已病入膏肓,我从美国赶回来陪着她。有一天姐夫骑着车带着大姐来探望娘,回家后又上街去,与别的摩托车相撞,没戴头盔的姐姐被撞成颅内出血。
虽经抢救保住一命,却从此再也没有从病床上起来自主行走过。
不久娘便去世了。在姐姐出事后,娘很快识破了我们欺瞒的计谋,可是曾几乎全能的娘已无力为她的长女做些什么。
临逝世前,娘也只是偶尔问起大姐,总忍不住叹息一声。
而今,爹走了,娘走了,大姐也走了。只希望他们天堂相见,能与往事,做一个彻底的和解吧。
遭遇车祸后,年近八旬的姐夫对大姐照顾得非常周到,几年中,每次我去探视大姐,都看得出姐夫的努力和细心。这也让我开始在心里认同了这个亲戚。
楚地旧习,葬礼会有一套流程,繁简不一。一般会请道士做一做道场。姐姐的灵堂内外照例排满花圈和各种经谶,灵前有道士们贴出的向大司命请路通谕的划有红圈的纸条幅。介绍着整个家族、后族(娘家)人的请求。姐姐的儿女孙辈跪在灵柩旁叩谢着前来吊唁的人。
我们余下的弟弟妹妹们也给大姐作了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磕头,四稽首间,我泪落如珠。
昨夜是最后的停灵,道士们吟唱起了“夜歌”。
与屈原的《离骚》同源的“夜歌”是汨罗江边古老的风俗。其内容是把逝者的生平或身边人的事即席成句,用低沉悠扬的固定调子唱出来。我一边听着偶尔有印象的往事,一边暗自打量坐在灵堂里的众人,想从中找到曾经见过的面孔。
没有,我认不出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他们都是在目前中国农村中最典型的面孔。
忍不住想起,姐姐终其一生与命运相搏,拼命守护着自己一点点用尽心力挣来的钱物,于她逝去的那一刻,其实全无意义。
而她丧失生命之后,又被我们送到了乡下夫家的山上埋葬。
那她这一生逃离农村的辛苦挣扎意义又在哪里呢?
送葬归来,在姐夫家门口的塘边,看见了一排正萌新叶的木槿——虽然我只来过两次,但这木槿我还留有印象。堂哥光明砍下了一把木槿枝条,说是要回去插枝。
这种木槿极易成活,不择肥瘠,插枝即成。它会开重瓣的各色花朵,浅白深红都有,花朵揉碎放入温水,是古而有之的极佳的洗发水。氽入滚汤,又是滑溜又清爽的美食。它的花期可以长达几个月,是江南极为常见的灌木。
看来明年春夏,可以在老家看到新开的木槿了。
一生起于微末之地,爱美而努力的大姐,不恰恰像一株在老家那片贫瘠的僻壤里长成的木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