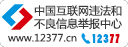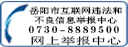□万岳斌
惊蛰过后,春雷一声喊,泥鳅欣欣然钻出泥地。泥鳅做菜,不养净有点苦。泥鳅炖豆腐,算得上本地一道名菜。可惜,之前没机会尝,有机会尝时我又不吃泥鳅了。不是泥鳅炖豆腐不会做,而是压根儿没人做。那时生活在乡下,山里豆腐也稀贵,泥鳅是泥鳅菜,豆腐是豆腐碗,两道菜断不会一锅烩。这样奢侈地吃,自己心不安,旁人也看不惯,忍不住要说你不会过日子,就算你海外有亲戚,也不带这样。淳朴的乡下人即使穷苦,一样看重名节,在乎别人的评价,生怕被指了脊梁骨。
吃得最多的,是母亲做的干辣椒焖泥鳅。焖到沸点,母亲站在灶台边,一手张开剪刀,一手捏着干红辣椒,“咔嚓咔嚓”,一小节一小节地剪落锅中。锅中一堆红后,锅铲翻动几回,盖上锅焖煮片刻。揭开时,沸锅冲出来的热气呛人的辣。隔几尺远闻到,鼻子一酸,“嗨哧,嗨哧”,最后那个喷嚏还没打完,鼻涕眼泪都出来了。
又热又辣的泥鳅入了口,辣得舌头在口腔里不得不咯咯转。实在受不住了,丢下碗筷,奔去水缸,舀起一瓢清水,大口咕噜咕噜喝下。不过,转回身又盯着个头大的泥鳅伸出了筷子,馋呗。

那时不明白母亲为啥要做这么辣,泥鳅又不用花钱买,稻田、溪水中弄罢了。我们嘟着嘴说太辣了,母亲不回应。下回做,外甥打灯笼照旧。其时母亲带着我们四张吃长饭的嘴在乡下,供养我们实属不易。虽然没有断过顿,但油盐汤做菜的日子也挨过。油盐汤,一小坨猪油一点盐,一些干红辣椒一锅水,便成下饭菜了。母亲算了又算过日子,不让我们时饱时饥,口里不说省着点吃,暗暗使“辣”计。看见我们辣得嘴唇发红,口腔里冒火星,母亲有一种爱意满满的无奈与心酸,心里苦苦的。只是我们的心思全在辣上而疏忽了。
乡下家里来了稀客,或者请了艺匠,配着其他荤菜,泥鳅才够格招待。那时最硬的菜是猪肉,其次是鸡、鸭、鱼。肥腻腻的、一咬油水直溅的猪肉任谁都爱,吃下去,力气马上就上来了。如今这样吃不健康,遭人讥讽“前世没吃过的”,那些日子里人都不嫌多。割猪肉得去肉食站,站里一天宰头把猪,还不见得天天宰。黑天光赶去排队,迟了,案板上连肉末、骨头渣都揩干净了,有钱都是空的。喂的鸡也不能随便宰,过年过节才会成盘中餐,抑或家里有人重病补身子用。平常指望它“果果嘎嘎”勤快下鸡蛋。泥鳅列在荤菜单里,却排在鸡蛋、豆腐之后。身价卑微的原因,无外乎野性生长,不耗费人力,自然不金贵;自身不带油星子,要扯了油香味才出得来,而猪油和茶油都得省着用。家里哪天有客造访算不准,没哪家条件允许先备着猪肉在。不得已,泥鳅翻身当主菜,主家惶惶然,又是解释又是赔小心,怕落得待人心不诚印象,毁了声誉。
村上有户人家,儿子定了亲,要预备着婚床等一应家具,请来闻名乡里的“木匠张”。那时嘛,艺匠师傅一般做上工不做包工,吃住在东家。因为要打制的东西多,天数估得不准,木匠进了门,又得一套手脚做完。这样一来,准备不足的尴尬就来了。几天下来,家里预备着的都吃完了。那天下午,女主人沏过热茶,招呼了一声便出门去了。过了半个来钟,额头渗着汗进了堂屋。手中一条方巾包裹,鼓鼓囊囊,右手提、左手托于身侧。见面便喊:“师傅歇哈啦,不在这点工夫。”边说边往里屋迈怕被瞧见。张师傅回话时望了一眼,心里明白这是找邻里借了鸡蛋。乡下邻里间互相借米借蛋常见,谁家都有应急时。过后还人家,互相帮衬着过日子。张师傅起早贪黑,从不歇晌,想尽快赶完工。“不累。晚上少弄点菜,吃不了好多的。”女主人的声音从屋内传出来:“冒么里招待,恁那嘎(您)不计较哦。”你看,先打过预防针。

掌灯吃饭,桌上最好的两碗菜,炸泥鳅、煎鸡蛋。泥鳅是头天要小孩子下田弄的。当小孩子的筷子再次伸向泥鳅碗,做娘的一声“嗯哼”,小孩子慌忙将筷子移开,夹了另一只碗里的虎皮辣椒放在饭上,受了委屈似的低着头,端碗起身要离座。做娘的喊住:“没家教啊。又不是叫花子。”小孩子只好斜着屁股坐下,眼睛里有荧光在动。张师傅心里明镜似的,夹上一条肚皮鼓鼓的泥鳅,戳进小孩子的米饭中,说:“吃吧。”孩子抬头望向母亲,做娘的对望了一眼,没说啥转过头捂住自己的鼻子假呛。再回转身,像突然想起什么来着,问张师傅:“听说恁那嘎不呷翘泥鳅的?”翘泥鳅,乡里土话,就是煮熟后身子弯着的。张师傅愣了愣,马上微笑接话,那语气非常肯定:“你听谁说了哦,把我的喜好摸得蛮清楚呀。”女主人笑了笑,脸色平静了许多,“这要搞清楚的,做了忌口的,不得罪恁那嘎了。”打那以后传开了,“木匠张”真的不吃翘泥鳅的。
到了家具城一家接一家开张的年代,自然而然,张师傅闲了下来。一天,发小与他拉呱,问他为何不吃翘泥鳅?他一支烟夹在手指间,叭叭叭连吐三个烟圈,讪笑着:“我有这么哈(傻),还做得好手艺?活泥鳅下热锅乱蹦乱跳,熟时都翘的,只有死泥鳅才是直的。我未必傻傻分不清,是翘的好吃还是直的好吃?哎,人家拿不出什么像模像样的东西招待我了。艺又没做完想省着点吃,我怕人家尴尬,只好硬着头皮应下来。应了东家就必须应西家,省得穿帮。”“那你那回在我家,也没有吃啊?”“你再弄出来,看我吃不吃。”发小本来想嘲笑他死要面子,听了这些话,半晌没作声。末了才低沉地回一句:“你心好!”
不记得是小学毕业那年还是上初一,班主任老师要到我同学家家访。同学父母是我的族叔族婶。叔婶头天知道后,便合计留老师在家里吃晚饭,叮咛我同学第二天务必将意思转达清楚。那时有知识的人不多,我们乡下特别敬重文化人,尤其是老师。老师来家访,感觉脸上有光。当晚天黑后,我那懂事的同学便提了一个柴火笼子去田里扎泥鳅。当时族叔罹患了很严重的肺结核,俗称“痨病”,瘦成了一根蒿棍子。腰佝偻着,走路拄一根竹杖,说话声音也变了。本是家里的顶梁柱,不仅废了一身武功,还成了一只药罐子。更要紧的是,病魔在身体里胡乱啃噬,三五餐便得来一回营养大补才缚得住那口气。故见到好菜喉咙里伸得出手来,恨不得一口吞下。邻里都晓得,但凡他家里有荤腥味飘出,过不了多久,他家准传出男女吵架声。再然后族婶呜呜地哭着跑出来,躲到邻里家或躲进菜园里抽泣,过了饭点才回。别人问她始终不说。族叔被阎王勾了簿,都道他享福去了,族婶抚着棺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灵,才哭出吵架原委,解了众人惑。心善的族婶有好吃的时借机吵闹,然后夺门而出,让他饱饱地吃,好留着这条命。只是苦了族婶,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一代。此是后话。

第二天下午,太阳从天井斜斜地照到了墙壁上。族叔将泥鳅倒进一只瓦罐,煨在火塘里,同时照看着吊钩上煮的饭,族婶在一边洗菜切菜。那瓦罐刚有热气冒出,族叔捕捉到那细微的香味,昏黄的眼睛顿时变得有光泽。他俯下身揭开盖,筷子在里面搅了搅。一会儿香气愈来愈浓,族叔用筷子夹起一条泥鳅,放进了口里,口中自言自语:“试试盐味。”再后来越烧越开,泥鳅翻上来沉下去。族叔像瘾君子见到了鸦片,夹上一条又一条,手不听使唤停不下来,全然忘了这是要招待老师的大菜。
向晚时分,同学领着班主任进了门。唠了一会,便上桌吃饭。乡下有敬菜的习惯,族叔夹起一条半截泥鳅,刚欲回带,在空中悬停了一下,放进班主任的碗里,嘴角有丁点往外扯,明显是在强忍着。他一个劲地催班主任吃泥鳅,班主任吃东西斯文,但架不住他的热情,只好将筷子伸过去。来回搅动半天,只夹到了一个泥鳅脑壳。班主任默默放下筷子,舀了几匙汤,端起来故意喝得呵呵响,做出一副好享受的样子。微笑着对族叔说:“我只喝汤。”饭吃下来,班主任再没伸筷子到泥鳅碗。他既照顾了族叔的体面,也咂巴出了我同学家的苦味。临起身时,班主任从口袋里摸出几张毛票子,不足一块钱,就着灯光抚了又抚,然后叠起放在族叔手掌上,将族叔的手指弯曲攥紧,嘱他去称点肉来补一补。族婶在一旁,边说“使不得,使不得”,边撩起衣襟拭眼睛。
这些与泥鳅有关的旧闻,逗人笑,然而笑过之后呢。我自离开家乡,几乎不曾吃泥鳅,说不出的缘由,是否因为其中含有的那份苦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