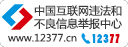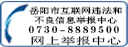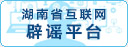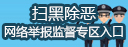□万辉华
40年前,我参加工作后,在单人宿舍,一度与人合住,在自己一侧的地方,安置了一个书架,请楼上善书法篆刻的室友,书了一个叫“苦竹斋”的模额,贴在墙上,俨然像一个书斋。虽然书不是很多,但是我很喜欢购杂志,加上单位图书室订阅了几十种文学和社科期刊,下班时,捎上几册带到宿舍。因此,爱读书的朋友喜欢到我的室内闲坐聊天,走时,借上一册杂志或一本书。
后来,由于迁到50平方米的宿舍,把“苦竹斋”这张纸揭下来,又请任美术老师的友人,画了一幅红梅中堂,贴在逼仄的住房。因住在五楼顶层,夏天极热,来宿舍聊天的朋友少了许多。我倒是不怕热,在斗室内,光着膀子,挥汗如雨,写出了一篇篇的散文、书评。某一年,赚了稿酬8000多元,要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为此,在宿舍走廊上自烧菜肴,请文友喝了一回“庆功”酒。
到2000年1月,我迁进了安居小区,建筑面积90多平方米,终于有了一间真正意义上的书房。摆4个书柜,仍放不下,只得把两个书架,放到客房里。这时,大约有了3000多册书籍,加上期刊,约有5000多本,因此我被评上了“岳阳市首届书香之家”。可是,是年秋天,我从郊区调入市区刚创办的《长江信息报》工作,白天在编辑部办公,遇上值班,晚上常常忙到凌晨才回家,我这个书房,也只有双休日才派得上用场。因书房坐北朝南,阳光甚为充足,坐在室内写作,一桌的阳光闪烁,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如蚕咬桑叶般清脆,一篇千字文,个把钟头就写毕。大多数文章,是为本报所写,偶尔给《中华读书报》《湘声报》等报刊杂志投稿,每月有几张稿费单飞来,让我买书又来了资金。
这时,我在报社的办公室也设了一个书架,陈列了一些工具书和政策法规类的书籍,偶尔有文友赠送的著作,也摆在架子上,抽空翻阅一下,为写书评作依据。因自己编辑了一个读书版,跑书店成了工作分内之事,每月要买几本书籍,杂志也是好几种。读毕的书籍,仍旧带回家中书房,不久,书柜被塞满,客房里书架和书桌也被堆满了。昔日在企业工作相熟的文友,知道我回了家,也约好到我书房喝茶聊天。
我的书房没有线装书,没有什么秘笈,最贵的书也不过几套上千元的,如《左宗棠全集》《郭嵩焘全集》都是托岳麓书社的编辑所买,十几册,标价不到2000元,给我打了折,也才几百元。
2018年秋天,我把家从郊区迁到市区中心,书房由一间变为了两间,一间在楼上,一间在地下室,楼上的书房,二十个平方米,楼下的也是。楼上的陈放湖湘文库,鲁迅、沈从文、钱钟书、李泽厚等中国文学大家,西方文学、文学理论及社科著作。楼下书房有岳阳籍作家、学者赠送的近300册书籍和现当代文学、新闻、历史、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书籍,还有4000多册杂志。2023年我退休后,在地下书房待了一个多月,每天工作半天,因夏天地下书房蚊子频频光临,没有装空调,坐久了热得受不了。我用笔把藏书分门别类做了登记,到目前为止藏书近万册,地下书房也装满了,我用纸箱装了两百本移到老家的房子里去了。
我的书房收藏着工作以来四十多年的日记,我发表文章的剪报,我的相册,甚至还有几十本样刊,以及订阅了四十年的《读书》《收获》杂志。我自创作至今仍旧订阅《中华读书报》,过去自做合订本,如今码在一起也是一人多高了。还有我从事新闻工作30年的荣誉证章。
这些都不值钱,却见证了我的阅读、写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