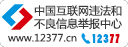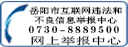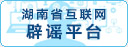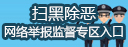□李 婷
记忆里的未解之谜
“妈妈,金鹗山有什么好玩的吗?”8岁的小雨一边往书包里塞零食,一边嘟着嘴问。妈妈笑着给她系好红领巾:“去了你就知道啦!
那是1998年的春天,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附属小学二年级的春游日。三十多个孩子像一群欢快的小麻雀,在金鹗山公园门口叽叽喳喳集合。班主任李老师举着小红旗,带着大家往山上走。小雨和好朋友小袁手拉着手,眼睛不停地东张西望,生怕错过什么“神仙”——毕竟传说这座山里住着金色的神鸟。
二十年后,已经成为新闻工作者的小雨在整理旧物时,翻出了那张泛黄的春游合照。照片里,全班同学挤在金鹗书院门口,每个人脸上都沾着冰激凌渍。她突然发现,当年和同学偷偷跑去“寻宝”的那棵歪脖子树,其实就在登山步道入口处——原来她们童年苦苦寻找的“神秘之地”,从一开始就静静等在那里。
今年春天,小雨约上已是两个孩子妈妈的小袁重游金鹗山。她们特意带了和当年一样的橘子汽水,找到那棵已经更加粗壮的歪脖子树,一待就是一下午……
这样的故事,几乎在每个岳阳人的记忆里都能找到相似的版本。金鹗山就像一位沉默的老朋友,见证着一代代人从童真走向成熟,而那些看似普通的春游记忆,经过岁月的沉淀,反而成了最珍贵的宝藏。

十年不变的“爬山帮”
今年清明假期的清晨6时15分,金鹗山南门的监控摄像头捕捉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画面:三辆私家车几乎同时停靠在停车场,走下来的不是装备齐全的登山客,而是一群穿着休闲装的年轻人。他们熟练地扫码入园,彼此打着招呼,像赴一场老友的约会。
“这是我们‘爬山帮’第十年的第N次聚会。”35岁的事业单位工作者陈州一边做着拉伸运动,一边开心地说。他身后站着七个同龄人,是从小学就认识的发小。
半山腰的亭子是他们的固定集合点。陈州指着亭子西侧第三根柱子说:“看这里,还有当年我们留下的痕迹。小时候春游,老师一说自由活动,我们就躲到这里分零食。”做新媒体工作的李炜从背包里掏出几包辣条,“现在每次来都要带这个,仪式感嘛!”这个自发形成的“爬山帮”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只要有约,必须是早上6时集合,雷打不动;上山还必须走最陡的东线台阶。
他们的坚持甚至影响了公园管理处。保安队长王师傅笑着说:“这些年轻人比我们上班还准时,冬天天都没亮,就听见他们在山脚下说笑了。”管理处后来特意加装了照明,还把他们常走的路线纳入重点清扫范围。
从小时候春游到中年爬山,一座山见证了成长,如今,爬山帮“扩编”了。陈州指着亭子里跑来跑去的几个小孩,“我们的孩子成了新成员。”他们给这个“2.0版本”的聚会起了个新名字:“爬二代俱乐部”。
据金鹗山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每天像这样组团来的团体至少有二十多个。他们大多由“80后”“90后”组成,还有“60后”“70后”。看着相似的聚会频率和专属路线,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他们用最孩子气的方式,守护着属于一座山、一座城的温暖记忆。或许正如陈州所说:“我们不是在爬山,是在找回家的路。”而金鹗山,永远在那里等着他们。

金鹗书院再现辉煌
清晨6时30分,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洒在金鹗书院的青瓦上,书院院长童童已经打开了那扇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红漆大门。令她意外的是,书院前的石阶上早已坐着几位等待的访客。
最早的金鹗书院建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在巴陵知县刘华邦的捐资倡导下,其规模参照了北宋六大书院之一的白鹿洞书院。江南才子吴獬曾任首任院长,他的智慧和才情为书院注入了勃勃生机。
然而,好景不长,民国初期的战火无情地摧毁了这座文化殿堂。书院被迫沦为兵营,所有房屋被战火焚毁,金鹗山上已无书院踪影。幸运的是,在1995年,得益于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的慷慨捐资和岳阳市政府的大力支持,金鹗书院得以在原址上重建。重建后的金鹗书院,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其作为“书院”的本性,但文化的根脉从未断裂。政府对金鹗书院的使用和发展高度重视,决心重塑其当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200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童曼娜女士与金鹗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她被书院首任山长吴獬的家国情怀所感动,也看到了百年书院的荒凉破败。她深知,自己肩负着重振书院的使命和责任。从2018年4月底开始,童曼娜女士倾尽所有积蓄投资500多万元对书院进行全面改造提升,克服重重困难,在著名学者、北京大学程郁缀教授的指导下,书院提出了“重振金鹗书院,共建文化高地”的口号,并由湖南浩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全面接管,这座古老的书院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如今,这座古老的书院在历经沧桑后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光彩,金鹗书院沉寂多年的辉煌再次重现,已然成为研究、学习、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地,并成为岳阳文化的新地标。
“金鹗书院正在成为岳阳的文化会客厅。”岳阳文史专家何林福评价道。这里既有白发老者来寻找青春记忆,也有年轻人来打卡拍照,更有家长带孩子来感受传统文化。这种古今交融的场景,正是书院生命力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