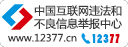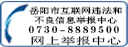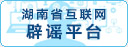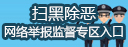岳阳学院教师 刘着之
2018年,作为记者的我捏着录音笔站在湘西一座百年祠堂前,耳机里循环着采访对象的方言:“我们的事,你们写字的人不懂。”那一刻,我想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言,“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而乡土的经验是比筛孔更细的粉。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1947年基于田野调查写成的社会学经典,以十四篇短文解剖中国基层社会:从人际关系如水波纹般由亲及疏的“差序格局”到依靠传统习俗而非法律维持稳定的“礼治秩序”,从“文字下乡”的困境到“长老统治”的机理。一部小册子,却犹如一双大手,剥开中国乡土社会的肌理,露出其中千年来未被言明的文化基因。
初读《乡土中国》,我划满问号:“差序格局”不就是人情社会吗?“礼治秩序”不就是封建残余吗?直到那天,我亲眼见证了那场比法院判决更有效的祠堂调解——两户村民因宅基地起了争执,可最后两家的男人在祠堂门槛前蹲着抽完一袋烟,族老把他们的酒碗碰在一起,酒液溅在族谱上,像又添了一代人的印记。原来这就是“无讼”传统的现代适应性,一如书中所言“乡土社会的权力,是教化性的”。
当都市人惯于用各种现代化标签简化乡村时,我们忽略了一种更细腻的“算法”——它计算的不是产权面积,而是世代相邻的情分权重。
这也成为我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不再用“落后/进步”的二元框架自以为是地解读乡土,而是学会理解它自洽的逻辑——就像费孝通笔下的差序格局,看似不够“现代”,却维系着无数村庄的呼吸与心跳。
如今,当我转换身份,站在讲台上,给我以启发的,则是《乡土中国》里那句“文字是庙堂性的”。我告诉学生:“你们要做的,是把祠堂里的故事‘翻译’给流量时代。”我致力于思考,如何更好地教会年轻一代用新技术去守护旧灵魂。
譬如,以往指导新闻专业工作坊时,我们放任学生自选题材——美食探店、城市夜跑、电竞比赛……虽然锻炼了技术,但总感觉少了些什么。直到重读《乡土中国》,我发现费孝通早已点破——“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我意识到,当00后们用4K摄像机追逐都市光影时,镜头背后那片更辽阔的土地,正逐渐失语。
我想,下一期工作坊,我们是否可以聚焦乡村振兴报道,只允许报道县域以下题材(非遗传承人、返乡创业者、村级“土专家”),并重构一些“乡村振兴报道工作坊”的规则:如48小时驻村,睡农家的硬板床,吃灶台的柴火饭;上几堂方言听力课,听农村老人用土话讲述乡土故事,再翻译成短视频字幕;开展反哺式创作,作品必须给被拍摄者审核,修改至他们点头认可……
值得欣喜的是,我们文学与传媒学院的广告学专业今年拟新增“乡村振兴广告传播方向”,这与我通过阅读而产生的思考不谋而合。未来,我计划参与两项研究实践,一是参与乡土品牌的传播研究,和学生一起探寻将富有湖湘特色的各种“土特产”变成“文化IP”;二是助力产学研联动,与本地文旅部门展开合作,把学生分组“承包”到县域,要求他们用几个月时间,为某个村镇量身定制从抖音脚本到农产品包装的传播方案。
书中说,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而我们的使命,就是帮助年轻一代在流量时代,重建对土地的记忆能力。偶尔在讲台上,我会想起湘西祠堂里那盏被风吹动的油灯。费孝通在1947年用钢笔素描的乡土,如今我们和学生正用镜头重新显影——那些被都市人称为落后的纹路:方言的韵脚、农具的木柄、葬礼上扬起的泥土,都将成为未来传播学的“源代码”。
我希望,今后的日子,在岳阳学院的实训室里,我们不做文明的判官,只做时空的接线员:让祠堂连接直播间,让米酒碰撞二维码,让祖辈的智慧永远在线。教育的真谛或许就在这里——我们教会学生使用摄像镜头,而土地教会他们,什么值得被看见。
(本文系岳阳学院首届“世界读书日教职工读书征文活动”一等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