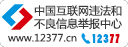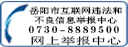□刘衍清
自古以来,岳阳城区西濒江湖,与湖北交邻,得舟楫之便,互通往来,语偏鄂音,而鄂音属西南官话语系。岳阳城区以东多由江西迁入,山路不便,与城阻隔,人多赣语。明朝中晚期乃至清末民初,交通渐便,东乡人涌入城南者多,渐成岳阳方言主流。
巴陵戏“念白”——岳阳老派方言的活化石
凡是听过巴陵戏“念白”的观众,总觉得其白话与现代岳阳人说话的声腔音韵不同,而与一些八九十岁的老岳阳人说话的语音相似。一般来说,地方戏的念白(又称“道白”)用的都是地方方言,如黄梅戏、越剧等,它与地方生活语言接近。巴陵戏的念白就吸收了在岳阳老城区流传了上千年的地方生活语言。一个地方剧种的念白就是一个地方方言的“活化石”。
元代戏曲家夏庭芝的《青楼集》中记载:“帘前秀,末泥任国恩之妻也,杂剧甚妙,武昌、湖南等处,多敬爱之。”岳阳乃湖北进入湖南必经之重镇,帘前秀是元末时期的北杂剧艺人,“驰名湖湘间”的演出活动,对湘北地方戏曲的形成是有影响的。明万历年间,比京剧还早的昆山腔风靡全国,至清道光年间,就有昆曲名伶徐三雅青居岳阳演出的记载。直到今天,巴陵戏还存有纯用昆腔演唱并采用岳阳城区老方言道白的传统剧目《天官赐福》。
据曾任湖南方言研究会会长李永明所著《湖南方言系列·岳阳方言》以及原湖南理工学院方言学者方平权所著《岳阳方言研究》和易本新所著《岳阳县方言》论述,岳阳自古为楚国疆域,而楚的中心处于长江以北。三国时先后属下隽和荆州管辖,而南北朝时设置的巴陵郡,以巴陵、下隽、蒲圻及江夏的沙阳县属之,这种跨江而辖的隶属关系维持了很久。由于岳阳通过水域与江北联系较多,而这些地区都属于西南官话语系,从而形成受西南官话影响的岳阳老派方言,又称巴陵腔或巴陵话。而老岳阳话通过巴陵戏这一媒介得以传承。
在岳阳城区,与岳阳老派方言形成对比的新派岳阳话则始于清末民初,是由岳阳东乡人渐次进入城区后形成的地方方言。岳阳楼有一副撰于清同治年间的长联写道:“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州城东道岩疆。”其中“岳州城东道岩疆”就是指岳州城以东大片的丘陵山区。由于交通闭塞,只有少量东乡人靠步行进城,而且在涨水季节又阻于横亘于城东南的南湖,仍得依赖舟楫才能进入城内。直到明清时期连接城区与东乡交通的南湖三眼桥修筑以后,才给岳阳东乡人进城提供了一些便利。因此,明清以前岳阳城区的居民基本上说的是岳阳老派方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仍有城北桃花井、柴家岭、翰林街、岳阳楼等直至城陵矶一带的老人说老岳阳话,与始于清代中叶的巴陵戏“念白”一脉相承。如巴陵戏道白中念城陵矶的“矶”为jì(去声),读“急”音,老岳阳话相同,而现在的岳阳话“矶”读平声。还有吃饭的“吃”,巴陵戏道白念成qì(契),现时的岳阳话念成qiā(呷)。
岳阳新派方言的根子在城南
清末民初,随着外来经济的活跃,岳阳城区迅速向南拓展,一大批东乡人涌入地势平阔的城南一带扎根谋生,从而把有别于城区土著方言的东乡话带入了城区。
按岳阳人传统习惯,以洞庭湖为界,湖以西称西乡,湖以东统称东乡。其实岳阳城东偏北的梅溪、昆山、平地、西塘等可称北乡;偏南的黄秀、长湖、荣家湾、黄沙街等属南乡。由于东边乡镇居多,加上京广铁路开通后,岳阳城里人更习惯将铁路以东统称东乡。
岳阳东乡话与大量江西的移民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客赣方言研究丛书》之一作者李冬香所著《岳阳柏祥方言》一书记载:岳阳东乡(含北片、南片)有姓氏339个,其中人口在1万以上的有刘、张、周、方、任、胡、王、黄、吴、易等10个姓氏的祖籍都是江西,如刘氏由江西瑞州府迁入,任氏、周氏、黄氏、吴氏均由江西南昌府迁入,易氏由江西吉州、瑞州迁入,因此受赣语影响较大。虽然岳阳地方方言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历来有“巴陵地土轻,十里换三音”之说,但基本发音及语义大同小异。尤其是新墙河流域的毛田、公田、月田、甘田、熊市、潼溪、新墙、筻口、龙湾、新开等地开发时间较早,人口分布均匀,相互通婚联姻,且人民自耕自足,受后来移民冲击较少,因而形成东乡话的主体。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从岳阳东乡进入岳阳城区谋生的人逐渐增多,其中到码头上当搬运工的东乡人数以千计,这部分人大都居住在城南韩家湾、红船厂、游击巷、洞庭庙、街河口等一带。日军侵华占领岳阳城区达7年时间,不少岳阳城区“土著”居民逃难在外,有的客死异乡,有的举家落户外地不再返乡,加上留在城内来不及逃走的难民也屡遭日寇杀戮。因此日本投降时,岳阳城区由3万多人锐减到2万人。为此又有一大批东乡人涌入城区,有的打工,有的做生意。20世纪50年代,为了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更多的东乡人被招进城区工厂和码头工作,而这大部分人也都分散在城南的大街小巷居住、工作,他们的子女也在城南读书生活。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城南一带就有岳阳师范、岳师附小、天岳山小学、塔前街小学、乾明寺小学、吕仙亭小学、贮木场小学、南津小学等,占岳阳城区就读学生三分之二以上。
半个世纪前,在县城为官的也大都是岳阳东乡人,他们的言语进一步推动了东乡话的普及。如1937年至1949年先后担任岳阳县县长的阮湘、黄继湘、方佩之、李毅仁、许新猷等都来自东乡的筻口、龙湾、毛田等地。1949年7月岳阳和平解放后,更多的东乡干部进入县城各机关部门,有的担任主职,如先后担任过岳阳县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毛致用就一直未改乡音。20世纪80年代初岳阳市、县分设,岳阳县治迁荣家湾之前,每年召开县、乡、村三级干部扩大会,都有数以千计的基层干部进入城区开会。台上作报告的、台下讨论的都是一片东乡话。因此东乡话基本上成为岳阳的地方“官话”。久而久之,原来的岳阳老派方言被压缩到极小的空间,说老岳阳话的只有极少的老年人。有的在家里与父母说巴陵腔,出门交往便说流行的岳阳话。5年前,作者曾发起一批有志者研究老岳阳话,好不容易找到陶武儒等几位老岳阳人录口音,但忙活了几年事还没做完,陶老先生就已作古。
稍晚于东乡人大量进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外来人口的迁入,岳阳城区还涌现了其他不同语系的方言。如位处城区最南端的省贮木场的工人大都来自湘、资、沅、澧四水沿岸山区,说的是“上湖南话”。位于城南磨子山、新印山的铁路职工家属来自五湖四海,说的是独特的“铁路话”。因铁路工作的需要,所有铁路职工都说的是普通话,但又各自带点地方口音。城南沿湖一线还穿插了港务局、水运公司、洞庭乡、南湖渔场、东风湖渔场、吉家湖渔场等。这些水上职工和船民、渔民大部分来自长沙、衡阳以及沅江、益阳、南县等滨湖各县以及湖北、安徽等省,口音各异。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们的二代、三代人也基本被新岳阳话所同化。
儿歌,岳阳方言的窗口
每个地方的儿歌几乎都是用地方方言唱出来的。由于代代相传的缘故,儿歌可以说是每个地方方言的窗口,通过儿歌可以深入了解一个地方语言的特色、文化传统和民俗风情。
在岳阳城南流传的儿歌是新、老岳阳话的融合体,以押韵的方式保留了岳阳地方方言以及市井生活的风貌。如:
三岁伢儿穿红鞋
三岁伢儿穿红鞋,
摇摇摆摆上学来。
先生先生莫打我,回去呷点奶汁(读“吉”音)来。
点子点波罗
点子点波罗,
洋人唱海歌。
青龙白虎十二个,不知点到哪一个。
乌龟打架壳压壳
牛打架,角抵角,
马打架,脚踢脚。
乌龟打架壳压壳。
点点虫虫飞
点点虫虫飞,
飞到嘎嘎(姥姥)屋里去。
嘎嘎不杀鸡,
扯到虫虫的衣。
嘎嘎不杀鸭,
扯到虫虫的袜。
米汤歌
不放盐,不放汤,
米汤泡饭喷喷香。
冇得鱼,冇得肉,
米汤泡饭胖嘟嘟。
注:“肉”和“嘟”字要读入声,岳阳方言的韵脚多读入声,方显其神韵。再如:
打麻将
胖子胖,打麻将,
该(欠)我钱,不还账。
左一棒,右一棒,打得胖子不敢犟。
缺牙耙
缺牙耙,灶里耙,
烟熏火燎眼睛辣。
耙到一块煳糍粑,恶(烫)到一个烂嘴巴。
金爹爹
金爹爹,卖蜜糖,
翘翘胡子像山羊。
金爹爹,做生意,
不是句好玩的。
岳阳城里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对金爹爹这位做糖人的老艺人都有印象。“不是句好玩的”既是称赞金爹爹的好手艺,同时也是告诫个别调皮小孩老实一点,拿了糖人不给钱小心金爹爹敲“丁公”(脑袋)。
还有一些无厘头的儿歌纯粹是用方言取乐。如:“肚子痛,毛毛拱,一哭一笑,王八搭跳。青皮抹抹苕,不打不长毛。火车来了我不怕,我跟火车打一架。打不赢,投我爷(读“牙”音),我爷甩我两嘴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岳阳方言儿歌体现了新老岳阳话的融合,但也有一些微妙的区别,如:
雁——雁——。
雁个一字我看看。
放酱油,打鸡蛋,
雁雁来吃油盐饭。
老岳阳话的“雁”字读平声,新岳阳话则读第三声(仄声)。
还有:“一扎狡里,落到交里。拿扎交几,切交狡里。”原意是“一只狗子,落到沟里,拿只钩子,去钩狗子”。这就纯粹是还没有蜕变的岳阳东乡话。好在从岳阳城南开始已传承了百余年的新岳阳话,除融合了日渐消失的岳阳老派方言以外,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吸收了不少常用的普通话发音,因此使得岳阳地方方言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使之能够在洞庭湖畔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