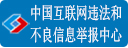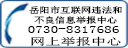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 1914-1984),阿根廷著名作家,短篇小说大师,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代表人物。1914年出生于比利时,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长大,1951年移居法国巴黎。1947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被占的宅子》,1951年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著有长篇小说《跳房子》,短篇小说集《游戏的终结》《万火归一》《八面体》《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等。1984年在巴黎病逝。

胡利奥·科塔萨尔
马尔克斯说,“翻开第一页,我就意识到,科塔萨尔正是我未来想要成为的那种作家”;博尔赫斯说,“无人能给为科塔萨尔的作品做出内容简介,当我们试图概括的时候,那些精彩的要素就会悄悄溜走”;聂鲁达说,“任何不读科塔萨尔的人命运都已注定。那是一种看不见的重病,随着时间的流逝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就好像从没尝过桃子的滋味,人会在无声中变得阴郁,愈渐苍白,而且还非常可能一点点掉光所有的头发”。
我们熟悉的世界仍有无数空洞,有待落笔描述。在科塔萨尔笔下,世界宛如一张折纸展开,内里的一重重奇遇让人目眩神迷。噩梦般的气息侵入老宅,居住其中的两人步步撤退,终于彻底逃离;乘电梯上二楼时,突然感觉要吐出一只兔子;遇见一个生活轨迹与自己酷似的男孩,由此窥见无尽轮回的一角……读过科塔萨尔的人,绝不会感到乏味。日常生活里每一丝微妙的体验,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即兴演奏,让你循着心底的直觉与渴望,抵达意想不到的终点。
本文题为《人见人爱的阿根廷人》,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94年2月12日在墨西哥城美术馆的演讲,本讲稿第一次发表于1984年2月22日,胡里奥·科塔萨尔去世后不久;科塔萨尔去世十周年时,曾作为纪念辞宣读;科塔萨尔去世二十周年的2004年2月14日,又在哈里斯科州的瓜达拉哈拉“又见胡利奥·科塔萨尔”座谈会开幕式上宣读。瓜达拉哈拉大学设有胡里奥· 科塔萨尔教研室,由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洛斯·富恩特斯主持。
人见人爱的阿根廷人
约十五年前,我最后一次去布拉格,同行的还有卡洛斯·富恩特斯和胡里奥·科塔萨尔。我们三个都怕坐飞机,便从巴黎乘火车前往,夜晚穿越东西德的时候,聊起两国无边的甜菜地、什么都造的巨型工厂、大战所带来的浩劫和肆意的爱情,总之,无所不聊。临睡前,卡洛斯·富恩特斯突然问科塔萨尔,是什么时候、由谁倡议将钢琴加入爵士乐的。他不过随口一问,想知道一个日期、一个人名,谁知竟引出一篇精彩的演讲,一听听到大天亮。我们大杯大杯地喝啤酒,大口大口地吃香肠拌凉土豆,科塔萨尔字斟句酌,深入浅出,从历史到美学,一一向我们道来,直到东方发白,才最终在对特洛尼斯· 蒙克的褒奖中结束。那长长的大舌音,管风琴般浑厚的嗓子和瘦骨嶙峋的大手,表现力可说是无与伦比。那个独一无二的夜晚所带来的惊愕,卡洛斯·富恩特斯和我永生难忘。
十二年后,我见胡里奥· 科塔萨尔在马那瓜的一个公园,面对着一大群人,用美妙的嗓音朗读一个短篇,是最艰涩难懂的那种——故事中不幸的拳击手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底层方言诉说着自己的经历。没在那种乌糟的环境待过,根本听不懂那种语言。可科塔萨尔偏偏挑中这篇,在宽敞明亮的公园里,站在台上,读给一大群人听。听众鱼龙混杂,有著名诗人、失业泥瓦匠、革命领袖和反对派。那又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尽管严格来说,即便是那些精通底层黑话的人,也不容易听懂这故事,但听众却能对故事中的情感产生极大的共鸣。可怜的拳击手孤零零地站在拳台上挨打,听众能感受到他的痛,为他的梦想和苦难潸然泪下。科塔萨尔与听众建立的是心与心的交流,谁也不在乎语言的含义,坐在草坪上的人都陶醉在这天籁之音里。
对科塔萨尔的这两次令我感触至深的回忆体现了他个性的两个极端,是对他最好的定义。私底下,好比在去布拉格的火车上,他博闻强记,侃侃而谈,风趣幽默,笑中带刺,能跻身于任何时代的杰出知识分子之列。而在大众面前,尽管他不愿做公众人物,可在无法回避的场合,他是那么非凡,那么细腻,那么奇特,那么令人着迷。无论哪种情况,他都是我有幸结识的令我印象最深的人。
第一次见他,是在一九五六年的悲秋之末,巴黎一家英文名字的咖啡馆。他时常去那儿,待在角落里,握着自来水钢笔在作业本上写作,手指上沾着墨迹。让-保罗· 萨特也在三百米外做着同样的事。当时,我已在巴兰基亚的朗塞旅社(每晚花一个半比索,与低薪的球员、快乐的妓女为邻)读过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翻开第一页,我就意识到他是我未来想要成为的那种作家。有人告诉我,他在巴黎圣日尔曼大街的“老海军”咖啡馆进行创作,我在那儿等了好几个星期,终于见他像幽灵一般飘了进来。他比我想象的要高,穿着一件长得要命的黑大衣,就像鳏夫穿的那种,一张娃娃脸被衬得有些邪恶,牛犊般的眼睛分得很开,斜的,清澈透明,若非心在驾驭,活像魔鬼之眼。
多年后,我们已是朋友,我又见到了他那天的样子。他在一部短篇佳作中重塑了自己:《另一片天空》里那个旅居巴黎,完全出于好奇而去断头台观刑的拉美人。科塔萨尔似乎是对着镜子写道:“他的表情很奇怪,既出神,又出奇地专注,仿佛一个在梦中停住脚步、不愿醒来的人。”故事中的人穿着黑色的长大衣,就像我第一次见科塔萨尔时他本人穿的那件。故事中的叙述者不敢上前去问他从哪里来,怕遭冷遇,因为如果碰到别人这么来问,自己恐怕也会生气。无独有偶,那天下午,在“老海军”,我也怀着同样的畏惧,不敢上前去问科塔萨尔。我见他不假思索、奋笔疾书了一个多小时,其间只喝了半杯矿泉水。
天黑了,他把钢笔放进口袋,作业本夹在腋下,像世界上最高最瘦的一名学生那样出了门。多年后,我们时常碰面,他与当年唯一的变化就是浓黑的胡须。他一直在长,却一直如出生时那般模样,直到去世前两星期,还像一个年华永驻的不老传奇。我从未壮起胆子问他,也从没跟他提起,一九五六年的悲秋,那个坐在“老海军”的角落、让我不敢上前搭讪的人是不是他。
我知道,无论他现在身处何方,都会骂我胆小。偶像让人尊敬、让人崇拜、让人依恋,当然,也让人深深地妒忌。而科塔萨尔正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唤醒所有这些情感的作家之一。此外,他还能唤醒另一种不太常见的情感:虔诚。也许,不经意间,他成了人见人爱的阿根廷人。不过,大胆设想一下,假若死者还能死,那么,眼下这种举世皆为他的辞世而悲的场景,恐怕会让他无地自容,再死一次。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书里,谁也不像他那样惧怕身后的哀荣、奢华的葬礼。更有甚者,我总觉得,在科塔萨尔心里,死亡本身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八十世界环游一天》中,一个人居然大出洋相——死了,朋友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所以,正因为了解他,深爱他,我才拒绝出席胡里奥· 科塔萨尔的一切治丧活动。
我希望能以如他所愿的方式怀念他,为他存在过而高兴,为我结识过他而欣喜。他留给世人的回忆犹如一部未尽的作品,是那么的美好而不可磨灭,为此,我心怀感激。
摘自《我不是来演讲的》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李静译
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1月

作者:〔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
译者:陶玉平、李静、金灿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被占的宅子》收录《彼岸》《动物寓言集》《游戏的终结》三部短篇集《彼岸》轻灵可爱,《动物寓言集》别致精妙,《游戏的终结》深邃离奇,科塔萨尔说:“我想创作的是一种从未有人写过的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