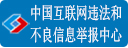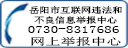前一段时间,笔者在电视上一档调解类节目中看到这样一个情节:一位离婚的父亲,曾在数年前离婚之际对刚满十八岁的儿子说:现在我可以不养你了,但在我年老的时候,你一定要养我。
电视上这位即将进入老年的父亲的话,乍听起来似乎没错,但仔细想想,又觉得不是滋味。他表达的意思是,十八岁儿子成年可以独立了,父亲便不再有抚养的义务,而子女赡养老人,则是中国的法定义务。
但是,在中国,年满十八岁的刚成年子女,有独立的能力和社会制度应给予的外在条件吗?且不说独立的那么一点点经济能力是否能应付如此物欲高涨的社会,就是六六四小学至大学的教育体制也不存在这个前提(“教育产业化”延长了学制)。总不能突然中断十八岁刚成年孩子的成长过程而让他们赤手空拳地走进这个物欲社会。哪我们这些长辈及延续的社会制度(所谓“上下五千年”了)还有存在和引为自豪的必要吗?
其实,电视中的这位父亲偷换了一个概念:把当今世界时代欧美国家“十八岁独立”的现实社会概念置换进了传统中国社会——历史中国从来没有“(十八岁)独立”的概念,以此来对接传统中国子女对年老父母“赡养”的法定义务。那么,既然对接了欧美国家“(十八岁)独立”,何不同时对接欧美国家无“子女赡养父母”(而是社会保障)的这个“法定义务”呢?——更把上下辈之间的情感因素偷换成了赤裸裸的利益交易(养育幼辈连禽兽也是这么做的)。或者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化讲究“孝道”观念,已经在千百年漫长的封建皇朝社会中被溺养成了“为老不尊”的文化因子?
这使得笔者想起了一百多年前清末曾经流行并一直在中国社会不自觉传承的一种思维习惯或说文化概念,这个概念叫“中体西用”,以西方国家的“用”为中国的“体”服务。对此,中国无数文化学者早已揭示:一者,它割裂了“体用”的内在一致性(清末大学者严复观点),只成为“为我所用”;二者,传承的“体用”观仍没有觉悟到何者为“体”何者为“用”(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观点,及,晚清谭嗣同早已指出:传统认为的“器”才是“体”,而“道”则是“用”,即后来发展出的“政治为经济服务”而非相反)。电视节目中这位父亲,其实就是清末“中体西用”经由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自我、自私需要的消化吸收而形成的一种观念应用的不自觉表达(在历史人类社会中,人性中的自私性具有巨大吞噬力量——西方文化已认识到这点,而中国仍沾沾自喜于“性善”论),即把欧美社会的“用”生搬硬套进了中国“体”(传统宗族性质中国的儿子不独立——接受家产和“赡养父母”看作一致性“体用”)。
长期以来,笔者一直不欲评论当今社会发生的一切人和事,只是因对当今社会人和事的困惑而去寻找它的源头。于是,笔者选择了一个离当今社会最近、也是对当今中国社会最有影响的晚清近代历史阶段,试图去解答“何以会如此”。
但是,尽管如此,笔者所引用的史实材料和所写史论观点,仍有被当今社会普众一直在不自觉传承的思维习惯所谓“借古讽今”所指认的嫌疑。何以会如此?
其实,就借古讽今一词说明,一,它承认了我们当今的社会形态和这个社会形态之下产生的人和事,和古代皇朝宗法社会形态之下的人和事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甚至有复制的一面。这就是历史学者们常说的“历史惊人相似”。当代中国仍没有完全脱离天圆地方的“天下”时代而释然自由地走进地球时代。假如把中国历史社会比作一页一页的书册,那么中国社会仍没有翻过此一页而走入彼一页,仍在续写着此一页,当然包括此一页中的旧观念、旧思维习惯和旧行为习俗。二,借古讽今一词无论是否确有其事,但作为一种普众性传承的思维习惯(出于同体性的讽者和指认者),说明它是由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历练而形成的,并被铸入讽者和指认者共同的不自觉意识中。显然这是确凿的,因为没有一个漫长历史阶段系统性的历练,人们(普通民众包括文盲)是不可能同体性地产生这种不自觉的思维习惯的。如果历史早已翻过了此一页,借古也就讽不了今了。
那么借古讽今这种思维和行为方式,究竟产生于中国历史哪一个阶段、以至于形成如此根深蒂固、中国社会上至学者下至普通百姓及文盲的同体性的一种思维习惯?
中国两千多年前始皇帝在统一中国之后,秦朝专权者、皇帝手下权臣李斯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事件“焚书坑儒”敕令中这么说过:长期以来的儒者学说就是“以古非今”。这个“以古非今”意思,只要有小学文化程度或者已经退化的高学历人都会知道,它就是指借古讽今或借古喻今。
李斯的判断没错。数百年前,当分裂的“东周列国”即春秋末期即将进入诸侯国战乱之际,儒学创始者便周游列国,竭力宣扬“克己复礼”,力倡西周初期“君臣父子”等级社会的礼乐秩序,并根据民间传说演义了一幅远古“尧舜禹三代”的美好社会蓝图,而他“美好古代”的言下之意,便是在斥责当时现实社会的丑恶。遥想一下,不知有没有哪个诸侯国君王采纳了他“仁”思想去面对丑恶、屠杀的现世,则确是“书生误国”和迂“老夫子”了——中国社会历来把“夫子”等同于空谈和迂腐也是始于同一时代和那一个对象。而面临秦朝大一统的美好形势,儒者们“以古非今”、厚古薄今的学说及思维方式,确实是现实统一“美好”秦朝的大害了。这也难怪和始皇帝登高望远、大好江山尽入一统手中的美好感觉相同的权臣李斯会给儒者们挖掘那么一个历史之“坑”了。只是可惜,有着社会同体性专制思维的李斯,最终也死在了专制之下——李斯们痛且快乐着。
秦朝之后汉武帝时代,对秦朝的“坑儒”进行了“拨乱反正”。曾经的“打倒”得到了“平反”——“坑”中之人飘然逸出;曾经的“下流”变成了“上流”;曾经的“楼下搬砖头”变成了“楼上人”;曾经的“仆人”变成了“主人”——中国历史社会在非主即仆的“普世观”中不屈不挠奋斗至公元二十世纪(非压迫即被压迫、非专政即被专政,在如此观念之下,缺乏团结的“一盘散沙”历史社会现象也就不难想象了)。自后两千多年不断更替的皇朝社会,都竭力打造儒者学说(因为儒学也历经多次衰微),而在打造之际,不经意间也把儒者学说“以古非今”、厚古薄今、借古讽今的思维习性同时打造进了中国的民族性格中;在历史上的民间社会,它主要体现在历朝的政治诉求如“反元复宋”、“反清复明”中。这也事实上强化了借大汉族主义滥觞的“借古讽今”思维习性。两千多年历史社会的滋养,使得中国普众即便是文盲都有了这种“大致如此”——惰性思维是愚昧的表现方式之一的不自觉思维习惯。至于什么是真正的是,什么是真正的非,不在这种思维习性之中(在皇一统权力之下,实际形成了无是非观)。
上个世纪中叶,中国社会产生了一个词叫“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是一个很不错、很有气派的词。但如果只是借“用”,而自己又翻不过“古”,那么得到的结果,也许会和自己的愿望相反了。借来的只是“用”,而正在滋养的一直是“体”,东施效颦,怎么看都不是滋味。应用于当代中国发展,就是借“用”了“加工业”而一直缺失“核心技术”(或称“基础技术”)这个“体”。中国只有在体制上而非说教上于纵向历史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于横向世界文化“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孙中山语)——离不开“学习”两字,才能取得令人赏心悦目的文化和实业进步,而非纠缠于古旧“体”和“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