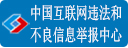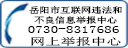【古典诗词,新鲜解读】
白居易《草》是赞美生命还是表达友情?
丁启阵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1
这首诗原题《赋得古原草送别》,也有叫《咏原上草送客》的。白居易生前对自己所作诗歌进行过多次整理、编集,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大类。这首诗被分在杂律类。从诗题“赋得”二字看,应该是应考的习作,题目是由他人指定、限定的,并非自选题目,有感而发。写作时,有诸多的讲究,诗句要切题,起承转合要分明,对仗须工整,等等。
2
《草》的写作时间,有说是贞元三年(787),即白居易十六岁时。
张固《幽闲鼓吹》:“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唐语林·赏誉》、《唐摭言》也有类似的记载。
《旧唐书》本传记载,“年十五六时,袖文一编,投著作郎吴人顾况。况能文,而性浮躁,后进文章无可意者。览居易文,不觉迎门礼遇曰:‘吾谓斯文遂绝,复得吾子矣。’”
但是,有学者根据白居易和顾况可考的行踪,认为十六岁作此诗的说法,仅为传闻,不可信。白居易十一岁(建中三年)至十八岁(贞元五年)在江南,十五六岁时(贞元二、三年),随父在徐州、衢州任上;而顾况,贞元五年以后即遭贬官饶州,不久又转至苏州。二人不可能在长安相见。再者,《幽闲鼓吹》、《唐语林》等笔记的记载,时间、地点多有明显错误,相互抵牾。有人认为,只有贞元五年(789),白居易曾去长安,两人才可能相遇。
这个问题,我有如下三点意见:
一、《草》诗白居易写于十五六岁上,是有可能的。白居易出生于父亲以上数代“世敦儒业,皆以明经出身”的家庭,早年的文化教育条件优越,早早学会诗歌写作,完全可能。《草》诗不是孤立现象,想要否定这诗写于十五六岁上,至少还事关相传作于十五岁的《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和作于十八岁的《病中作》等。
二、证明白居易十五六岁没有游历过京城,不是容易事。有句话:说有易,说无难。仅凭白居易十八岁前生活在徐州、衢州等地,便断言他不可能见过顾况,难免武断。年代久远,文献记载有限,白居易早年的行踪,今天所能知道的,也只是一鳞半爪,远非全貌。
三、即使白顾贞元五年前没有见过面,顾况欣赏白居易才华、因白居易之名开个玩笑,也完全有可能。人没有相见,诗作可以传播。顾况读到白居易的诗作,说句俏皮话也合乎情理。
3
《草》诗所表达的是什么思想,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唐诗三百首》的编辑者孙洙(蘅塘退士)认为:“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是比喻小人。“野火烧不尽”,比喻小人是铲除不尽的。“春风吹又生”,比喻小人会随时出现。“远芳侵古道”,指小人侵犯正道。“晴翠接荒城”,指小人文饰鄙陋。
《唐诗鉴赏辞典》:“……烈火再猛,也无奈那深藏地底的根须,一旦春风化雨,野草的生命便会复苏,以迅猛的长势,重新铺盖大地,回答火的凌虐。看那‘离离原上草’,不是绿色的胜利的旗帜么!”(周啸天撰文)显然,这是把《草》视为生命的赞歌。
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呢?
我认为,两种说法都不对,都违背了诗歌本意。
这是一首送别诗。诗意所在,是末联“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两句诗的意象源自《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只是经过了转化,把怀归的意思转化成了送别之情。说白了,就是以春草比喻友情。春草蓬勃表示对送别对象的情谊深厚。
前四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写景,不过是回溯动态之景,并非眼前静止之景。等于把春草发芽、生长的过程给复原了。这样写的好处是,生动有趣。五六句,“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相当于上世纪初李叔同(弘一法师)填写的《送别》歌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乃是送别时分的眼前之景。“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用的是移情手法,萋萋芳草成了对远行朋友的留恋之情。艺术手法上,跟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把滔滔江水想象成对远行朋友的留恋之情,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见,把诗题《赋得古原草送别》改为《草》,并不恰当,还不如改为《送别》更切题。
4
白居易的这一首少作,既渊源有自,又源远流长。上溯可以追到《楚辞·招魂》“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可以追溯到南朝梁刘孝绰妹的:“落花扫更合,丛兰摘复生”,可以追到孟浩然的《春中喜王九相寻》:“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刘商(大历年间进士)的《柳》“几回离别折欲尽,一夜春风吹又长”;往后,有宋人释惠崇的《访杨云卿淮上别墅》:“河分岗势断,春入烧痕情感”。
有这些渊源关系,同时也就有臧否。宋人范晞文《对床夜话》认为刘商“几回离别折欲尽,一夜春风吹又长”,不如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语简而思畅”;称有人认为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如释惠崇的“春入烧痕青”。
这类臧否,见仁见智,无可厚非。但是,有一个事实谁也无法否定: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最为家喻户晓。从措辞文雅蕴藉的角度讲,释惠崇的“春入烧痕青”的确有过人之处,但是,白居易因为是少年之作,更加率真自然,别有风致。有如前人所说的,“一句之意,分为两句,风致亦自不减”(清田雯语),“不必定有深意,一种宽然有余地气象”(清屈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