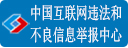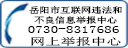作为香港影人的典型代表,徐克最根本的“心法”,是用时尚的特技效果和明艳的演员质感来展示暴力背后作为人性基质的“抒情”与“侠义”。到了2017年,同为解构主义者的徐克与周星驰在《西游伏妖篇》中依然延续了这一“抒情”的意旨,只是在浓烈情感的铺垫上做得太过仓促,也没有黄金时代女演员的倾情演出作为核心品质的保证,在邪典感与暴力感方面的营造也因为虚构神魔故事的基调而显得缺少指向性。但这依然是一部很徐克的电影,观众也应当更多地看到精彩纷呈的武打与特效背后的东西。

《西游伏妖篇》
近年来,老牌香港电影人往往尝试推陈出新,在自己过去的影像风格之上增添新的时代感。徐克、周星驰合作的正是这样一部两位殿堂级电影人的实验之作。但是,这种试图面对新时代审美需求的“实验”的力度也许不够。整个影片中依然贯穿了旧式港片“无厘头”与“重口味”的交响旋律,然而,在浓烈的当代商业片的环境影响下,这部电影获得的口碑未必尽如人意。原因在于,两位大导演的粉丝往往也会同时将此片与他们过去的创作进行比较对勘,这使得这部略显仓促的娱乐影片在立意与结构上的光泽显得格外黯淡。
这种“影响的焦虑”首先在于,周星驰《大话西游》所营造的奇幻苍茫本质上是不可复制的:其背后一代人的彷徨落寞在当代并非靠浮华的视觉奇观所能再现。然后,徐克出于各种当代电影的特殊考虑,把注意力放在了特技场面之上,最后做出了一部中规中矩的商业片。在光鲜亮丽的审美维度方面不落于任何同代人后的同时,这部电影一旦被放置在徐克过去带有强烈革命实验色彩的作品序列里,就会显得过于平庸。

周星驰和徐克
此外,时至今日,要说哪一位电影人能够彻底代表香港电影的全部风格,首屈一指的候选人当属徐克。在过去近四十年里,徐克为电影爱好者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十多部可供反复品味的经典作品,还是一种独特亮丽、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美学品质。从其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处女作《蝶变》(1979),到最近获得广泛讨论的《智取威虎山》(2014),徐克的电影题材纷纭、内容驳杂,让人从一般娱乐类型片的角度难以给予分类和评价。
但人们都清楚地看到,在徐克过往的作品里,自始至终贯彻着一个主题,那就是对“江湖”这一中国独特的政治社会组织形式的观察与再现。徐克的电影,无论其背景是在古代、近代还是现代,无论其题材是武侠、神鬼还是警匪、传奇,都试图通过夸张、奇崛、诡怪的浪漫主义电影语言展现一种远远不同于过去文艺影视叙事中的“江湖”的图景。通过对新题材和新语言的开掘,徐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过去正统江湖叙事背后的伦理尺度进行一定高度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一般将徐克的作品视为“新浪潮”,视为香港电影中最具革命性的一道风景。
要理解徐克的“革命性”,就得首先看到他在什么意义上继承并超出了过去的江湖视觉效果营造者们的思路。在这方面,最值得对比的,就是香港江湖叙事的大宗师张彻在6、70年代奠定的“暴力美学”的影像基调。在张彻的《报仇》、《十三太保》、《马永贞》等经典作品中,男性阳刚身体在施加和承受暴力时爆发出的直观感性体验往往得到视觉上的直接渲染,并构成一种风格化的影视语言。张彻擅长用宏大漫长的打斗场景,搭配主人公壮烈牺牲时的慢镜头乃至于定格,凸显“男性气概”,并由此把由崇高肉体承载的“义气”、“尊严”、“忠诚”、“豪迈”的伦理品质用最简练有力的影像留映在观影者的记忆深处。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不难发现,张彻的暴力美学是对宋元明清以降民间小说戏曲的艺术表现方式的重新发挥,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就义”这一贯穿中国古典时代的场景的深刻继承:从《春秋》、《史记》中的义士与刺客,到《三国》、《水浒》中的猛将和豪杰,张彻鲜活地用现代影像技巧再现的,正是这一儒家忠义正统叙事中的审美与伦理逻辑。
但在徐克的武侠作品中,这种正统叙事将迎来更多的反思和讨论。首先,在张彻那里,有力男性的气概和身体是绝对的主题,女性只是情节催化剂和点缀。在徐克这里,除了女性角色通常承担核心叙事功能之外,“女性”本身也成为了电影试图彰显和探讨的美学品质。《蝶变》中的米雪、《上海之夜》(1984)中的张艾嘉、《倩女幽魂》系列(1987-1991)中的王祖贤、《刀马旦》(1986)、《东方不败》(1992)中的林青霞、《青蛇》(1993)中的张曼玉……由这些一流女演员用绝妙气质与绝世容颜撑起整体惊艳效果的徐克电影,整体上也就构成了一种别样的女性气质宣言。与此同时,我们会发现,徐克电影中的男性主角大多是以陪衬的形象出现的,在江湖故事中,其所彰显的品质与其说是刚猛有力、沉稳内敛,不如说是风流儒雅和幽默不羁。这也就让我们发现,与张彻相比,徐克的“新”首先在于:人类的复杂多样的性情得到了更多维度的呈现和抒发。
基于这样的性情呈现逻辑,相比起张彻,徐克电影中时刻彰显的与其说是暴力的崇高与壮美,不如说是对男性身体所承载的暴力机制本身的批判。相应地,通过对微妙且错综复杂的“人情”的描写,关于暴力之下脆弱个体的自由与解放叙事得以展开。如果说张彻的暴力影像是对小说、戏曲等传统江湖传奇叙事的现代“模仿”,那么徐克电影中幻美与阴鸷交杂、香艳与残酷同调的氛围,则是对传统的解构和重新创造。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说,以徐克为代表的“新浪潮”的本质,就是以香港本土的文艺立场,对以张彻为代表的南渡一代影人的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与20世纪后半叶光怪陆离的现实政治经济局势更加契合,从而构成一种面对新市民阶层的集体抒情机制。
建立在以上两点观察的基础之上,我们不难看到徐克看似眼花缭乱的影像主题与技法背后一以贯之的美学伦理结构,从而能在他的电影创作史中梳理出一条更加清晰的思想轨迹。
让我们从被人们广为称道的“混乱三部曲”说起。以古代为背景的武侠片《蝶变》、以民国为背景的恐怖片《地狱无门》(1980)和以当代为背景的警匪片《第一类型危险》(1980)所讲述的主题是一致的:基于暴力而形成的“江湖”、“宗法乡村”和“当代社会”等政治系统,最终也会被暴力所毁灭。徐克在这三部电影中确立了他对暴力的呈现艺术和批判主题。

《蝶变》
《蝶变》的故事主线是武林霸主十色旗主田风、女游侠青影子和武林史官方红叶三人受沈家堡主沈青所托,保护其不受神秘的杀人蝴蝶诅咒之害,在破案过程中,三人揭示了沈青与天雷堡制造火枪凶器的阴谋,最终田风和青影子与阴谋家同归于尽,唯有毫无武功的文人方红叶以旁观者的身份全身而退,记录下整个事件的始末。影片一开始就用旁白介绍了武林中的两次血流成河的大厮杀和后来长期的互相敌视状态,这显然是在影射20世纪的现实世界局势。徐克通过奇幻意象隐晦表达出对现实中的暴力杀戮在整体上的摈弃:具有驭蝶本领的沈夫人就像美丽的蝴蝶一样,因人性的丑陋而成为阴谋的帮凶和牺牲品;俏丽机敏的青影子本有机会逃脱暴力的漩涡,却因过强的好奇心成为无辜受害者;田风的高傲与天雷堡的野心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与方红叶的明智恬淡则构成鲜明的对比。总体上来说,《蝶变》超出了过去武侠叙事中强调的“功名”与“复仇”的逻辑,通过美好女性形象的消逝反过来凸显暴力政治的可怕,并以一个具有高超智慧的江湖知识人方红叶的视角俯瞰整个杀戮的江湖,展开属于他自己的叙事。这个孱弱又清醒的知识人,显然就是亲身见证了越南战争、并在70年代末试图对冷战局势展开反省的徐克本人的精神寄寓。

《地域无门》
相比起《蝶变》中的隐晦批判,《地狱无门》则通过对鲁迅《狂人日记》中核心意象“吃人”的直观影像呈现,对“五四”以来国民性批判精神进行继承和发挥。《地狱无门》讲述的故事是:一个隐蔽村落“大家乡”的村民以吃人为乐,保安队长决定着人肉的分配权;侦探“九九九”为了追捕大盗劳力士来到此地,与小偷包铁胆在村中遭到多次袭击;最后“九九九”战胜保安队长,带着女青年阿莲离开村落,却发现阿莲已经染上吃人心脏的无可救药习性。这个简单的故事被血腥夸张的杀戮场景和疯狂无厘头的插科打诨扩充成了一种彻底的狂欢:“大家乡”里的大多数乡民都是愚蒙无知的状态,受到保安队的管控,以分到人肉为唯一的生活寄托,教书先生四处偷肉吃,村长还假惺惺地为被吃者做法事。显然,徐克是借此延续鲁迅的路径,对中国民众、知识人和官僚的麻木不仁与自我欺骗进行讽刺。保安队长作为独裁者,杀人如麻的同时又在夜里偷偷翻阅《寂寞的心》,这是在挖苦历史上的“独夫”统治者缺少基本社会能力。保安队副队长劳力士作为外来人是唯一具有正常思维的乡民,但却被“九九九”视为恶人追捕,而“九九九”作为正义暴力的象征,却毫无智慧可言,一直受到保安队长的蒙骗;唯有明显是喜剧小丑角色的小偷包铁胆却显得有智有谋——这一系列人物群像都反映了徐克对传统政治社会格局的正面形象的颠覆:空有“高大全”的暴力英雄,无助于瓦解黑暗,唯有喜剧幽默精神,能够作为对这种虚伪格局的彻底对抗。徐克特地让长相酷似鲁迅的高雄饰演吃人元凶保安队长,让酷似毛泽东的徐少华饰演英雄“九九九”,并让二人在“大家乡”的宗祠中对打,甚至出现了“关云长上身”的“神打”桥段,无论其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构成了极强的现实指涉性。在影片最后,美貌的阿莲从人腹中捧出仍然跳动的心脏的画面对“西子捧心”的传统审美尺度进行了解构。这一意象延续了《蝶变》中女性美好形象坍塌的叙事逻辑,让《地狱无门》在美学上获得了纪念碑式的历史地位。事实上,明眼人可以看出,徐克的这一系列影像设计的灵感源泉都在于鲁迅在早期的社会政治批判小说中营构的黑暗乡土中国形象。也因此,《地狱无门》在继承了“五四”时期的启蒙精神同时,也将其中妖魔化、丑化传统中国的偏激因素用港式闹剧的方式毫无节制地表达了出来,这也就为香港电影中强烈的解构主义无政府倾向客观上提供了一种呈现方式。

《第一类型危险》
到了《第一类型危险》中,徐克将现实批判的视角直接放置到了当代,让不谙世事的学生和心理阴暗的底层少女工人联合成无政府的炸弹狂魔,并安排他们不自觉地走向被社会彻底排斥的恐惧,并最终遭遇真实的罪恶如本土黑社会和跨国犯罪集团等的迫害。《第一类型危险》在对暴力的奇诡表达的强度上远远高于《蝶变》与《地狱无门》;与此相伴的,则是青年学生们无知无畏和后知后怕的深度的心理透视。整部电影中贯穿着狂野的青春期躁动与对世界格局的针砭,但其中最为关键的元素则是某种正面凸显出来的暴力批判和社会关怀。通过对几个炸弹犯罪者在罪恶之路上越陷越深的过程的极端迷狂式的情节表达,尤其是通过叙述少女迷恋暴力却最终在暴力之下肉体与灵魂都支离破碎的命运,徐克完成了他对古往今来暴力叙事的集大成的呈现与解构。尽管如此,徐克的这部电影却客观上促成了暴力叙事在技巧上的进步,无论是犯罪集团制裁过失人员时的酷刑,还是影片最后的墓场枪战,都构成了让人恐慌的永恒视觉经验。
“混乱三部曲”是徐克风格的开端。在其中,不难看到欧美与日本电影在主题和技法方面的影响。《蝶变》部分取材于日本推理片如《八墓村》;《地狱无门》则受到《生人勿进》、《天师捉妖》之类的西方恐怖片的影响。 这个时候的徐克正在探索属于他自己的叙事之道。这样的探索在后来的《笑傲江湖》(1990)、《倩女幽魂》、《东方不败》和《黄飞鸿》(1991-1993)系列中得到了延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混乱三部曲”之后,徐克一改其作风,进入到了一种“拜女教”的影像癖好当中,这在《新蜀山剑侠传》(1983)中以飞天形象登场、后来又在《刀马旦》中男装示人的林青霞和《上海之夜》中活色生香的张艾嘉和叶倩文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徐克笔下的女性开始获得强烈的个性与尊严气质,影片中往往用大量的空间来表现女性和女性之间的情谊,除了给予女性演员更多自我彰显的机会,还让影片整体上具备了老少咸宜、温馨甜美的抒情氛围。
这种对女性的重视体现为两点。首先,相比起胡金铨苦大仇深、义无反顾的“侠女”,相比起张彻影片中作为“契机”和“点缀”的女性,徐克在电影中让“奇女子”获得了一次新的解放:女性开始成为电影的核心人物,其独特夸张的情绪和个性构成了电影发展的根本动力;反过来,男性角色则成为辅助与衬托。比如,在《刀马旦》中,比起林青霞、叶倩文和钟楚红三人角色的生动,郑浩南饰演的角色仅仅是线索型男主角;又比如,尽管在《上海之夜》里钟镇涛具备相当的重要性,但整个故事的主线则是围绕张艾嘉和叶倩文两人的友谊而展开;在《打工皇帝》中,与其说许冠杰、泰迪罗宾和徐克本人扮演的打工仔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不如说扮演资本家千金的王祖贤更加能够获得观众的好感。到了《笑傲江湖》中,徐克彻底颠覆了名义上的导演(也是徐克本人在念书时的研究对象)胡金铨的思路,加入大量表现女性身体、性格和嬉笑狂欢的情节,除了让影片更加通俗化、趣味化之外,实则也给予了女性演员叶童、张敏、袁洁莹等人发挥抒情表演技巧的空间,营造了别样的审美氛围。至于后来的《东方不败》和《风云再起》则更加明确地以林青霞、王祖贤、关之琳、李嘉欣等女星的“美色”为卖点,用大量的浮夸剧情与特技烘托出诡异至极的影像效果。与此相应的,则是男性角色的丑角化、恶劣化和扁平化。可以说,徐克根本没有将太多的心思放在男性角色的建构之上,无论许冠杰还是李连杰,“令狐冲”这一形象在徐克的“江湖”中所起的作用和《蝶变》中的方红叶一样,都只是旁观者和探索者,只是为了完全讲述并展现故事而存在并行动着。《风云再起》中于荣光扮演的顾长风则是这种旁观者的典型代表。相应地,女性形象的天马行空式的惊艳呈现,则更加有效地引起观影者对美好与温柔、浓情和洒脱的共情机制。

《倩女幽魂》
但在同时期的《倩女幽魂》系列中,男性的视角则得到了一定的加强。原因在于,这些男性并不是江湖中人,大多凸显出“读书人”和“修道者”的非凡形象,进而具有一般男性并不具备的自我反观透视的能力。在《倩女幽魂》第一部中,被两个剑客用剑指着、夹在中间的宁采臣显然就隐喻着冷战局势中的文化人。由张国荣以婉约中带有韧性的声音与演技营造的“路随人茫茫”的氛围则让观影者意识到徐克强烈的政治隐喻并未在日益繁荣发展的香港社会局势中消逝,而是以更加精致奇幻的方式呈现出来。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人间道》和《道道道》里,这种隐喻伴随着女鬼、修道者、妖魔鬼怪等角色的矛盾冲突得到了更加显著的呈现。王祖贤扮演的女性幽灵形象总是遭受邪恶势力的监禁、屈辱和压迫,与此同时,拯救这一女性幽灵的任务落在青年迷茫者和另一种正义暴力的担当者——除妖者的身上。“有情”的港式主题,则是所有人物得以建构信任合作关系的根本动机。

黄飞鸿系列

新龙门客栈
随着时势的变化,在之后的《黄飞鸿》系列和《新龙门客栈》中,一种类似张彻电影中的男性形象也在逐渐回归,并以身体搏斗的明快意象来承载进步战胜落后、启蒙超越愚昧的现代性叙事。无论是象征官方专制的宦官特务(代表腐败暴政的阉人的形象也贯穿着徐克作品,其符号意义十分固定),还是象征民间迷信的邪教组织,都被象征洋务运动以来中国近代化进步叙事的主人公黄飞鸿一一击败。在《狮王争霸》中,黄飞鸿对李鸿章的著名劝谏集中反映了徐克启蒙叙事的基调。徐克在《黄飞鸿》系列中对武斗暴力的表现达到了新的高度,但对武斗暴力的批判也是不遗余力。通过塑造黄飞鸿这一传统武学集大成者在时势中自我更新、启蒙并创就新气象的过程,徐克把传统的德性品质和近现代历史有机地融贯在了一起。由于其显著的历史现实主义的主题,女性的叙事作用再次降格到男性之下。

《智取威虎山》
至此,不难发现,在徐克电影中(甚至可以认为在整个香港当代电影史中),男性形象的功能往往和写实的、历史性的主题紧密相关;女性形象的凸显,则和抒情的、奇幻或传奇式的故事内容发生联系。在神怪主题的《青蛇》和传奇主题的《新龙门客栈》(包括《龙门飞甲》)中,活灵活现的女性形象总与浓情蜜意紧密相关。在《智取威虎山》中,男性气概在枪林弹雨与机锋暗斗中的公式化展示则是为了让历史获得最大程度的合理化解释。徐克就此穿插在两种气质之间,在批判暴力世界的同时又在艺术的维度将暴力世界美化、神化,这种暧昧当然只是他的电影语言的表层信息,其最根本的“心法”,则是用时尚的特技效果和明艳的演员质感来展示暴力背后作为人性基质的“抒情”与“侠义”。
到了2017年,同为解构主义者的徐克与周星驰在《西游伏妖篇》中依然延续了这一“抒情”的意旨,只是在浓烈情感的铺垫上做得太过仓促,也没有黄金时代女演员的倾情演出作为核心品质的保证,在邪典感与暴力感方面的营造也因为虚构神魔故事的基调而显得缺少指向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徐克的独特美学品质没有延伸到这部电影的一些细节当中。正因为如此,在观赏徐克电影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更多地看到精彩纷呈的武打与特效背后的东西,尝试去观察导演是否还能在挥洒自如地娱乐观众和严肃真诚地保存传统之间找到“中道”,是否还能以更加敏感的历史视野去体认那一抹红妆素裹的情义,并将这一延续了四十年的独特的民族影像经验永远地保留在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