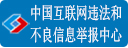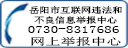我的家乡在岳阳市经开区西塘镇新屋葛家。父亲葛正达老先生,母亲陈湘如娭毑。都是解放军总后离休老干。
我们葛家正在续序家谱。我的远房堂兄葛大德先生接受了为我的父母写传记的任务。大德兄是副教授,他又为我出了一道作文题,要我们兄弟姊妹五人,每人写一篇纪念我父亲葛正达老将军和母亲陈湘如老将军的文章。我谨遵兄命写了这篇小文章,以缅怀我的爸妈。
我是1955年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十一医院(现在的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从我有记忆到小学二年级,跟父母的时间是聚少离多,因父母工作很忙,我在幼儿园、小学住校,所以每周只有一天时间在家里。即便这样,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我自认为父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从未向组织索取什么,而是全心全意地努力为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总是为别人着想,宁可自己吃亏,也要帮助有困难的人。
1963年秋,我爸因工作需要调到天津工作。当时组织上分配我们住在大理道一处三层小楼,我家住在二层。小院环境很好,离我父亲的办公地点只隔一道墙。但没住多长时间,我们就搬到睦南道一个大杂院里一层楼分散的房间,离办公地点也远了。后来才知道是我爸将好房子让给了一位新搬来的与他同级的干部,我家才搬到大杂院的。我们本来是可以不搬的,把条件好的房子让给别人,我母亲也支持我父亲的这一举动。当时我不理解,母亲告诉我吃亏是福。搬到大杂院后,当时只有我们家里有电视,我父亲为了让大家都能看上电视,把电视放在一楼大厅里,后来一楼大厅装不下人了,又把电视搬到单位的活动室。当时每晚院里院外的人都来活动室看电视,父亲就把家里的电视交给了单位公用。但是我们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1964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放学回家,进屋以后看到一个妇女躺在我的床上,身边还有一个婴儿。当时我心里很不乐意。后来妇女的家人来接她,并送来很多礼品以表示感谢,我母亲拒绝接受。原来是这位妇女要生产,人力车拉到我们院门前时,产妇就要生了。这时正好我母亲碰到。母亲毫不犹豫把她接到我家里,进家门时婴儿的头已经出来了,我母亲马上帮助接生,我父母都是医学教授,保证了母子平安。当我看到产妇一家人对我母亲的感激之情时,我心里也舒畅多了。
母亲对我的教育很严格。她经常告诉我人要知足,知足者常乐。我们家虽比上不足,但比下有余。助人才能有乐。她是这样教育我们,同时也是这样做的。
我爱我的爸妈。他们都是老一辈革命家。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我是他们的小女儿,学工科的,现在在首钢大学任教。请家乡父老乡亲,旅游北京时,到我家来做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