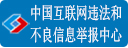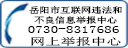在中国传统中,过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人生慰藉。
当一个人慢慢长大,岁月会冲洗掉许多回忆,但有关过年的记忆如同“最后一片叶子”,哪怕斑驳,却也总不掉落。在那个短缺的农耕时代,平常的日子都是黑白的、无声的,唯有过年是彩色的、喧闹的——有红色的春联和窗花、有震天的爆竹和锣鼓……
过年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过年是安逸的、享受的、充满梦想的。过年尤其是孩子们的节日,对成年人来说,过年没有了新鲜感,也就失去了值得记忆的价值。成年以后,我对过年的印象与平常没有什么两样,甚至照样早晚喝稀饭,天黑就睡觉。如果说起小时候过年,那我对过年的记忆就是劳作,从腊八一直忙到正月十五,几乎没有几日得闲——
每年过年,别人家里都在赶年集,置办年货过大年,我们一家人都要借着年关忙生计:腊月里没日没夜地磨豆腐,到年根上全家出动卖门神,一直到大年三十;过了初五,又开始编灯笼、糊灯笼,初七以后赶集去卖,卖到十五后晌集散,才能回家吃一顿安生元宵,这算是过完了年。
同样过年,从古至今,不同的人对过年都有不同的感受。过年是奢侈的,对穷人来说,常常连年都过不起。即使如今,虽然温饱无虞,但过年基本的团聚却成了一种奢侈。很多外出打工的成年人和他们的孩子,实质上都过不起年,买不到票,回不了家,见不到自己的家人。那句“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更多时候是一种无奈和安慰。
那时候,俺爹常说:“富人过年,穷人过难。”意思是说,过年这事情,富人有富过法,穷人有穷过法;对最穷的人来说,没钱过年,反倒害怕过年,就像《白毛女》中的杨白劳一样。有时俺爹会把这句话换成“富汉子过年,穷汉子挣钱”。中国人看重年节,平常再节俭,过年也要大大方方地花钱置办年货。这在那个前消费时代,年关无异充满巨大的商机。因此,勤快又眼活一点的穷人可以趁机从富人手里挣点辛苦钱。
每年冬季,俺家都会因为磨豆腐熬豆浆而烧穿几口大锅。豆腐做出来放在院子里冻着,第二天天不亮,我和我爹就起来,用扁担挑着两屉豆腐,分头去周边村里“串乡”,一般不到晌午就能挑着空担回来。我那时候已经十几岁,还没有变声,童音嗓子吆喝着卖豆腐,如同小公鸡打鸣一样,经常被人笑话。
相比之下,我还是更愿意去卖门神。
门神
文革时期,传统年画和乱弹一样,都被禁了。每到过年,人们都从新华书店里买新式的油印年画,家家炕上都贴着《红灯记》《龙江颂》《奇袭白虎团》等样板戏的画张。到了我上中学,乱弹开禁了,但传统年画已经绝迹了。以前被批为“封建迷信”的土地神、灶神和龙王又重新被家家户户供起来,过年贴门神成了一件大事情。国营书店里不卖门神,传统的凤翔雕版手工印刷的门神画便热销起来。
人民公社时期户户家徒四壁,人穷得连院墙都没有。毛死后,人开始能吃饱饭了,随着人民公社完蛋,家家都筑起了院墙,装上了新漆大门。有了新大门,没有门神自然是不妥的。
跟着一个亲戚,我去凤翔进了一批门神画,还有各种土地神、灶神、仓神、天神、龙王等神像画,然后背着书包赶集去卖。刚开始,一张版画进3分钱,卖5分,后来涨到7分进,卖一毛。卖门神的好处是分量轻,装在书包就能行,可以去比较远的地方。远一点的集市很少碰到熟人,这样就不怕人笑话。那时候我总认为摆摊卖东西是一件害臊的事情。
年集人多,总要起很早赶去占地方,去晚了就没有好地方摆摊(摆在偏僻的地方,就卖不出几张画)。赶集要早,常常鸡叫头遍就要起来;有时去的集市远,鸡不叫就被娘从被窝拽出来,迷迷糊糊地吃点东西就上路了。那时候自行车是奢侈品,我家里穷,买不起自行车,一家人也都不会骑自行车,多远都靠两条腿走。爬高上低,走上几十里路,最后棉鞋都踏湿了,蹲在集市上刚一小会儿,凉气就从脚心往上冒。
门神画都是印在白纸上,需要一张张摊开,好让人们看清不同的印工和纸质,选择自己喜欢的画——这叫做请神。卖门神最怕刮风,尤其怕雨雪天。风大会吹乱摆在地上的画,集市都是土路,一会儿就会在纸上落一层厚厚的尘土。要是碰上雨雪,那几乎就没法摆摊了,满街都是泥,画沾上雨滴就会马上洇了颜色。
那时节集市没有水泥路,如果冬里下过一场雪,一两个月地面都是湿的。为了防止地上的潮气洇了画,常常要铺上一张塑料纸。卖东西不能来回动弹,一天下来,手脚都免不了被冻伤。有时候半天没人问津,好不容易来个人“请神”,手麻脚木,连画都拿不起来。有几次因为没有占到好地方,一天下来连一块钱都卖不到,不够交工商税费的。天黑时回到家,饥寒交迫,一头扎到炕上,啥话都不想说。那时候,我常常想起《卖火柴的小女孩》那篇课文。
灯笼
过年少不了灯笼。
当时传统的手工灯笼已经很少了,大多都是南方纸品工厂大批量生产的圆灯笼和折叠灯笼。我爹也试着进了一些这样的“洋灯笼”来卖,结果卖不出去,只好白送给村里的娃娃,说到底庄稼汉人不那么擅长做卖买。
按照关中习俗,大年三十“接”先人,正月十五“送”先人,先人的坟头要挂上一只红灯笼。传统上,这种红灯笼都是手工编的,外面糊了一层红纸。编灯笼用的不是竹篾,而是高粱杆破成的篾。为了编起来更柔韧,篾一般先用水煮过,趁热来编。
比起寒风中卖门神来,坐在热炕上编灯笼要幸福得多。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谝着闲话,比赛看谁编得快,炕前的炉子里咕嘟嘟煮着篾,一屋子热乎气。
编好灯笼,再往上糊红纸。因为每个人用力不同,编得灯笼大小不一。每个灯笼用的红纸大小也不一样,红纸过大不行,过小也不行。在当时家里看来,人工不要钱,篾也不值钱,唯独红纸最金贵。一大张红纸能糊17到20个灯笼。我当时已经念到中学,先量不同灯笼的尺寸,然后计算好,一次裁出五种不同规格的红纸,一大张红纸一点儿也不浪费,最多时一大张红纸可以糊出22个灯笼。有一次我不在家,我爹只好自己裁纸,结果留下一堆没法用的红纸,不是太短就是太窄。他不得不承认:“念过书就是不一样。”
比起编灯笼来,卖灯笼其实就很省事。一背篓灯笼,背到集市上,一会的工夫就卖完了。一只灯笼卖5分钱,后来几年涨到一毛钱。有一年元宵节,俺爹坐在炕上算账,十天下来,卖灯笼总共挣了120多元。在我想象中,那可是一笔巨款。我趁机要了5元的学费。因为这120元中有我的贡献,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向俺爹要学费而不会被骂。
故乡
从七八岁记事起,每年过年都这样,不是磨豆腐卖门神,就是编灯笼卖灯笼。那年我考上中专,寒假回家要坐几天几夜火车。一到家,就换上棉袄磨豆腐。村里人见我卖豆腐回来,就笑话我说:“吃上商品粮了,咋还卖豆腐哩?!”确实,村里其他几个考上学的人,每天都西装皮鞋偏分头,在村口晃来晃去地显摆呢。
在外地上学远比中学时花钱多,即使过年时全家人忙得不分昼夜,最后还是凑不够我下一学期的生活费,这让我离家的一路上心里都非常难过。
俺爹那一代人从大饥荒中侥幸逃生,后来大半辈子被禁锢在人民公社下的生产队,跟奴隶囚徒没有多大的区别,一年起早贪黑,累死累活,到年底一算账,还欠公家的钱粮。暴力与贫穷是一对孪生子。生产队里弱肉强食,批斗械斗暴力几乎是家常便饭,俺爹脾气不好,家暴多,唯独每年过年,他都一脸和气,对谁都笑嘻嘻的,也爱讲笑话。所以过年也是个难得的太平日子。
后来父亲去世,兄弟姊妹长大各自成家,我一个人流落远方,过年时匆匆打个来回,家变成了老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情景就再也没有了。
有一年我娘腊月扫舍,在箱子底找到了十几张陈年的门神灶神,我看见就要走了,权当留个念想。现在老家过年,年画都是激光彩印的财神像,油光瓦亮,就连门神也改为现代油印了,传统手工雕版印刷的门神很少见卖;偶尔见到,一般也都是印在宣纸上,装在镜框里,俨然变成了猎奇收藏的旅游纪念品。
如今十五去上坟,坟头的红灯笼都变成工业生产的大红灯笼。那种老式“鬼灯”已经很少有人做了。我娘每年还是会自己编了几个灯笼,只是送给邻居和亲戚自用罢了。